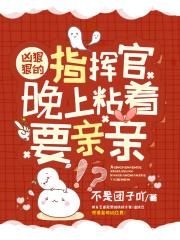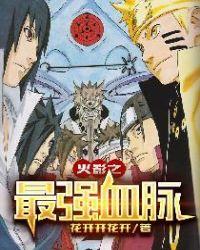笔趣阁>水浒开局在阳谷县当都头 > 第433章 给他就是了都给他了他就满意了(第1页)
第433章 给他就是了都给他了他就满意了(第1页)
浑身甲胄两三层的武松正在笑,哈哈狂笑:“杀!”
手中硕大的朴刀,已然不是刀,就是一根加长版的大铁条,左右打砸,嘭嘭作响,被击中之人,没有一个还能在倒地之后站起来。
还有那掷弹兵他身后铁甲之。。。
冬至的晨光如薄纱般洒在开封城头,林昭伏于屋脊,望着远处宫墙之上袅袅升起的烟雾。那不是炊烟,也不是香火,而是梦监台崩塌后残留的血雾,在寒风中凝成细丝,缠绕着飞檐翘角,仿佛整座皇城都在低语呻吟。
沈小砚蜷缩在瓦瓮后,双手紧攥炭笔,指尖发白。他昨夜梦见了铁盒残片上的裂痕突然蔓延,化作一张巨口,将整个汴京吞入黑暗。醒来时,怀里那块金属竟微微发烫,像是回应某种遥远的召唤。
“他们已经开始清洗。”林昭低声说,目光落在街角一队穿黑袍的“清心营”士兵身上。他们正挨家挨户搜查,凡家中藏有非官定典籍者,不论老幼皆被拖出,戴上静音枷押走。更有甚者,只因孩子背书时多念了一句《孟子》中的“民为贵”,便被当场杖毙。
沈小砚咬唇,眼中怒火翻涌。他掏出怀中薄纸,疾书一行字:“我们不能等了。”
林昭点头:“是时候了。”
计划早已拟定??不攻宫门,不举义旗,而是以声破梦。他们要让真相像瘟疫一样,在沉默的人群中悄然传播。记述使们已潜入各坊间,将《辨诬集》拆解成街头俚语、茶馆评话、乞儿歌谣;还俗僧人则联络旧日江湖势力,组织“哑者会”,专收被施加静音枷的读书人,教他们用手势与图画传递文字。
而林昭的任务,是在最热闹的地方,讲一场没人敢听的故事。
当晚,相国寺前的灯市如常开启。彩灯高悬,鼓乐喧天,百姓却行色匆匆,不敢驻足交谈。林昭换上褪色锦袍,怀抱琵琶,带着沈小砚登上临时搭起的说书台。台下稀稀落落坐着十几人,大多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和聋哑乞丐。
“今日不说传奇,不讲鬼怪。”林昭拨动琴弦,声音不高,却穿透寒夜,“我说一段真事,名叫《阳谷冤录》。”
人群微动。
“话说大宋宣和年间,山东阳谷县有一都头,姓林名昭,为人刚直,不畏豪强。一日巡查市井,见一妇人披发跣足,跪于衙前哭诉丈夫失踪。经查,其夫乃县城卖饼小贩,因私下议论蔡京新政弊端,竟被西门庆勾结县令秘密拘捕,投入枯井……”
沈小砚蹲在一旁,迅速将话语转为图画,画在一块木板上:一个男人坠井,井口站着笑嘻嘻的官员与富商。几个孩童凑近观看,眼神渐亮。
林昭继续道:“林都头查明真相,欲为民申冤,却被反扣‘煽动民变’之罪,险些丧命。他逃出生天,写下第一篇《冤录》,从此踏上执笔之路。”
说到此处,琵琶忽转悲调,如泣如诉。人群中已有老人默默抹泪。
忽然,一名黑衣人闯入人群,厉声道:“禁说妖言!速速散开!”
围观者顿时惊慌四散,唯有那群流浪儿不动,反而围得更紧。
林昭抬头,平静地看着对方:“你说这是妖言?那你告诉我,阳谷县当年是否真有此人失踪?西门庆是否真的霸占他人妻室?县令是否受贿枉法?若皆属实,何来妖言?”
那人语塞,正欲动手,却见四周屋顶跃下数条黑影??是“哑者会”的兄弟们到了。他们手持竹竿长绳,封锁四方出口。
沈小砚猛地举起木板,上面新增一句:“你们怕的不是谎言,是有人记得。”
林昭站起身,朗声道:“我不是一个人在写《冤录》,我是替千千万万个不敢说话的人执笔!你们以为烧书就能灭忆?割舌就能止声?可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真相就不会死!”
话音未落,远处钟楼传来三响??那是宵禁的信号。
但他们已不在乎。
当夜,整个开封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无数纸鸢从贫民区升起,每一只都挂着微型油灯与手抄片段,《辨诬集》的内容随风飘扬;街头巷尾,盲童口耳相传一段神秘歌谣:“阳谷都头未曾亡,执剑录里写苍凉。若问光明何处起?万家灯火读文章。”
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佩戴静音枷的囚犯竟开始用指甲在墙上刻字,内容竟是《执剑录》节选。守卫发现时,那些字迹仿佛有了生命,顺着砖缝蔓延,如同藤蔓攀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