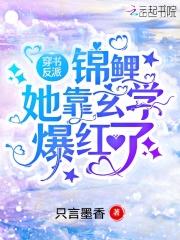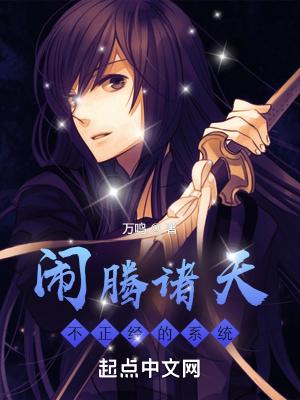笔趣阁>水浒开局在阳谷县当都头 > 第444章 天下皆士(第1页)
第444章 天下皆士(第1页)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宗泽、张叔夜、李纲之辈,兴许感受不确切,但吴用感受已然是刻骨铭心!
吴用心中有一个问题,天子为何如此区别对待?
天子自是心中有答案的,但不可能告诉吴用,所以,吴用着实想。。。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沈小砚离开汴京那日,天未明,星犹在。他独骑瘦马,背负一只空陶罐,沿汴河古道缓缓北行。身后城楼灯火渐远,如同退潮的萤火,而前方晨雾弥漫,仿佛天地初开时那一片混沌。潘姓少女本欲随行,却被他劝止:“你留下,把‘问’种进庙堂。我在野,你在朝,一阴一阳,方可长久。”
她站在城门口,手中紧握一卷尚未誊抄完毕的《问录?续解》,望着那孤影没入薄霭,终不回头。
自此,沈小砚不再以师者自居,亦不称都头、不提旧职,只自称“行问人”。他穿行于黄河故道、太行山径、齐鲁荒村、燕北边镇,每至一处,不设坛、不聚众,唯于茶肆酒坊、渡口驿站、田埂灶前,与人闲谈几句家常,然后轻轻抛出一个问题:
“你觉得,雷为什么打在穷人家屋顶多?”
“你说,官府断案,是依律法,还是依老爷的心情?”
“若有一天,孩子问你‘爹,咱为啥要跪’,你怎么答?”
这些问题如细针扎入厚茧,无声无息,却让听者夜不能寐。有人怒而拂袖,有人冷笑离席,也有人默默记下,传给儿孙。更有农妇将问题写在布带上,系于井绳;牧童刻于树皮,随风飘向远方。
半年之后,民间悄然兴起一种新俗:每逢月圆之夜,百姓便自发聚集村中老槐或石桥之下,点燃一盏油灯,轮流讲述自己心中最不敢问出口的问题。起初不过三五人低语,后来竟发展成千人围坐、万人传声。这些集会无人组织,却自有秩序,被称为“问夜”。
而与此同时,“启元新政”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地方豪强勾结残余清心卫,暗中焚毁学堂、迫害讲问士子;某些州府官员阳奉阴违,将“疑经科”改为背诵圣谕考试;更有藩镇节度使上书弹劾潘姓少女“蛊惑圣心,动摇国本”,要求将其贬为庶民。
面对压力,潘姓少女并未退缩。她在国子监设立“问谏院”,广招寒门子弟,亲自授课,并命人将《百无一用问录》印制成册,免费分发至各县私塾。她还在宫中发起“静室对谈”,邀请三品以上大臣轮流入殿,不议政事,只回答三个问题:
你是谁?
你怕什么?
你希望你的儿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许多大臣初时搪塞敷衍,但在连续数次对谈后,竟有人痛哭失声,自陈多年阿谀逢迎之罪,请求辞官归田。也有武将坦言:“我带兵三十年,从未想过为何而战。”自此开始研读《问典》,甚至主动请命前往西北边陲,重建被战火摧毁的义学。
然而,真正的风暴,来自北方。
补天军攻陷幽州后,并未南下直取汴京,而是屯兵长城沿线,整编各族部众,建立“共议庭”,凡重大决策皆由各部落长老、士兵代表、流民首领共同商议决定。韩定远亲自主持首场议事,议题竟是:“我们为何而反?是为了夺权,还是为了让人人都能说话?”
会上争议激烈,有将领主张立刻南征,“挟大胜之势,逼皇帝禅位”;也有渤海遗民代表怒斥:“我们不是来当新皇帝的奴才的!”最终决议:暂缓进军,先在北方十州试行“民议制”??每一县设“问政亭”,百姓可随时登亭发言,意见汇总上报,官吏若拒不回应,即遭罢免。
消息传回汴京,朝野震动。宰相怒斥此举“乱纲倒纪”,礼部尚书更称其为“蛮夷之政”。唯有潘姓少女沉默良久,而后提笔写下一道奏章:“昔者三代之治,始于乡校议论。今日北地所行,非叛逆,乃复古也。”
就在此时,西北传来急报:敦煌莫高窟第17窟密室开启,出土一批唐代手稿,其中赫然记载着一段失传已久的《问经》残篇:
>“天不言,故令人问;地不语,故令人思。问者,生之机也;思者,存之道也。禁问者,杀未来之人;惧思者,葬已死之国。”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批手稿的最后一页,竟绘有一幅地图,标注七处地点,与当年阳谷山腹七洞窟位置完全吻合,且旁边批注一行小字:
>“七问之枢,藏于水底。待有心人拾之,则天下再无可封之口。”
这封密报被连夜送入皇宫,年轻的天子独自在灯下读完,久久不语。次日清晨,他召见潘姓少女,低声问道:“你们……真的找到了‘问’的力量?”
她答:“陛下,我们只是唤醒了它。它一直就在人心深处,像井底的月亮,看似沉寂,实则常明。”
天子长叹:“朕昨日梦到父皇。他说:‘守住江山。’可我现在想问??江山是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