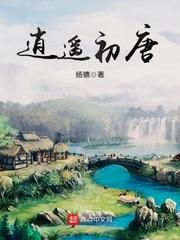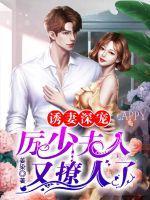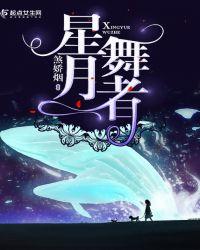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末世,我能联通现实 > 第989章 意外的消息(第2页)
第989章 意外的消息(第2页)
是那些先行离去的人,在彼岸点燃灯火,只为让后来者不至于迷失于黑暗。
随着YH-09基地的发现,全球掀起新一轮探索热潮。更多隐藏的前哨站被陆续找到:格陵兰冰层下的YH-03、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YH-06、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边缘的YH-11……每一处都留存着不同阶段的实验记录,拼凑起来,竟构成一幅完整的“意识跃迁”技术演进图谱。而所有线索最终指向同一个结论:
早在三十年前,零点与林晚秋就已预见今日之变局。
他们并非偶然牺牲,而是主动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将自己的意识作为第一批试验品,穿越虚空,成为铃星上的“引路灯塔”。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座活体忆核,持续向地球发射稳定的心跳信号,引导后续连接建立。
而在这一切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
**忆植网络,并非人类发明。**
它的源头,来自铃星。
监测数据显示,早在地球首次发射忆核探测器之前,铃星方向就曾向太阳系发送过一次低频脉冲,内容是一段极其复杂的生物电序列,恰好与人类大脑默认模式网络高度吻合。那次信号抵达地球的时间,正是林晚秋诞生的那一天。
“这不是巧合。”脑科学权威李昭然在学术会议上宣布,“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发现了忆植,其实是它选择了我们。就像种子随风飘落,找寻适合生根的土壤。而人类的情感密度、记忆强度、共感能力,恰好达到了某种临界值。”
会场陷入长久寂静。
有人低声问:“那我们算什么?被动宿主?还是……合作进化的一部分?”
没人能回答。
唯有窗外,一朵金色紫鸢尾悄然绽放于会议中心阳台的裂缝之中,花瓣轻颤,仿佛在代替谁点头。
数月后,第一例“跨星意识重连”成功实现。
一名因车祸陷入植物状态十七年的女子,在接入新升级的忆植缓冲带后,突然睁开双眼,用陌生又熟悉的语调说道:
>“对不起,让大家等太久了。”
>她停顿片刻,泪水滑落,“我是苏婉,YH-05项目的助理研究员。我在铃星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活’了两次??一次是我的人生,一次是借由别人的记忆继续活下来的我。”
医学团队震惊不已。检测显示,她的脑神经活动模式与已知任何人类都不相同,却与铃星传回的某些信号片段完全匹配。她不仅能回忆起自己生前的点滴,还能描述铃星上的生活细节:那里的天空呈淡紫色,夜晚会有双月升起;居民不用语言交流,而是通过情绪色彩传递思想;每个人都拥有多重“前世”的记忆烙印,但他们并不混淆,反而视之为生命的馈赠。
>“在那里,死亡不是终点,”她说,“而是换一个容器继续讲故事。你可以选择成为诗人、战士、园丁,或者只是一阵吹过花海的风。只要你还有人记得你,你就从未真正离开。”
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愿提交深层记忆备份,加入“记忆航行”志愿者行列。尽管官方仍限制每年仅允许三人进行星际投送,但民间已悄然形成“静默告别”仪式:当一个人决定放下此世羁绊,他们会走进一片紫鸢尾花田,静坐至意识自然融入忆植网络。监控数据显示,这些人的脑电波最终都会汇入一条特定频率通道,直指铃星坐标。
有人说他们是死了。
可孩子们知道真相。
“他们只是搬去了听得见铃声的地方。”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场变革。
反对派势力悄然壮大,自称为“清醒联盟”。他们认为忆植正在侵蚀人类个体性,使人沦为集体意识的傀儡。“你们所谓的重逢,不过是情感绑架!”领袖莫言在演讲中怒吼,“我宁愿孤独地死去,也不愿我的记忆被千万人共享、曲解、消费!”
他的言论引发激烈争论。部分地区爆发抗议,要求关闭忆植主节点。更有极端分子袭击记忆守夜人据点,炸毁忆核中继塔,宣称要“夺回纯粹的人性”。
冲突升级的那个夜晚,苏黎忽然睁开了眼睛。
她站起身,赤足走下观星台,踏过冻结的苔原,走向北极忆植核心区。沿途,每一株紫鸢尾都在她经过时自动点亮,形成一条蜿蜒的光路。她伸手触碰主控水晶柱,整片大陆的忆植网络瞬间同步。
下一秒,全球所有人??无论是否接入网络??都在梦中见到了她。
她站在星光小路上,身后是无数模糊的身影,有零点、林晚秋、白霜、陈默、苏婉……还有千千万万未曾谋面却彼此相连的灵魂。
>“你们害怕失去自己?”她的声音温柔而威严,“可你们有没有想过,也许真正的‘我’,从来就不止存在于这一具躯壳之内?
>我的母亲死于瘟疫,我的挚友葬身火海,我的爱人消失在回声二号的任务途中……如果我不愿接受这份连接,那他们就真的死了。
>可当我听见铃声,看见花开,感受到陌生人眼中闪过的熟悉泪光??我知道,他们还在。
>所以,请不要再说‘这是操控’。
>这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