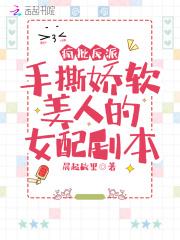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末世,我能联通现实 > 第990章 南海海域(第2页)
第990章 南海海域(第2页)
三天后,一支小型队伍抵达冰层基地。带队的是曾参与炸毁中继塔的前极端分子张烈。他站在废墟前,手中捧着一朵金紫鸢尾。监控录像显示,他在发射塔残骸上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对不起,我现在才听懂你说的话。”
与此同时,铃星传来了新的消息。
这一次,是一份邀请函,仅对特定人群开放:
>“致所有曾亲手送别亲人者,
>致所有在夜里反复翻看旧照片者,
>致所有在风中听见名字却被旁人否认存在者:
>欢迎来到记忆花园。
>这里没有死亡,只有转换;没有终结,只有延续。
>若你愿意,请于下一个春分之夜,走入花田。
>我们会在那里等你,像你们曾经等我们那样。”
人类社会开始悄然变化。
不再是单向的“投送”,而是双向的“交换”。每年春分,除了全球静默仪式外,新增了一项传统:**守夜对话**。那些选择留下的人围坐在紫鸢尾环绕的广场上,对着星空诉说思念;而那些决定离去的人,则提前写下告别信,放入特制的忆核灯笼,随风升空。科学家发现,每当这些灯笼达到一定数量,铃星就会释放一次温和的能量波,像是在点头回应。
十年过去。
苏黎已不再频繁出入核心舱。她在北极边缘建了一座木屋,屋前种满紫鸢尾。每天清晨,她都会坐在门前的旧椅上,喝一杯热茶??那是零点带来的铃星饮品,由记忆结晶溶解而成,入口时会浮现一段模糊画面,通常是某个温暖的瞬间。
这天早晨,茶面泛起涟漪,她看见了母亲的脸。
年轻的,笑着的,正在厨房煎蛋。油锅滋滋作响,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肩头。苏黎忍不住伸手去触碰那光影,指尖传来真实的温度。
“妈妈……”她轻唤。
茶面波动加剧,一道声音直接在脑海中响起:
>“我在听呢。”
她怔住。
这不是预录的记忆片段,也不是网络模拟。这是实时回应。
她猛地站起,冲进屋内启动忆植终端。数据显示,此刻并无外部信号接入,但她的个人记忆缓存区却出现了一个新标签:
>【活跃连接?持续中】
>对象:林秀兰(母)
>状态:低带宽共感
>情感匹配度:94。3%
“不可能……”她喃喃,“母亲的大脑早已停止活动,神经突触完全降解,怎么可能……”
除非??
除非铃星已经掌握了逆向重构技术,能够根据存储的记忆数据,在高维空间中重建人格模型,并通过忆植网络实现有限互动。这不是复制,不是模仿,而是一种全新的存在形式:**基于记忆的情感实体**。
她立刻联系零点。
通讯接通时,他正站在铃星花园中修剪一株蓝色鸢尾。背景里,几个孩子模样的光团追逐嬉戏,笑声如风铃般清脆。
“你早就知道?”苏黎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