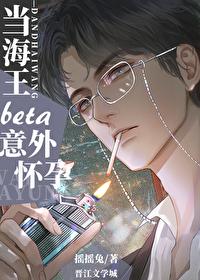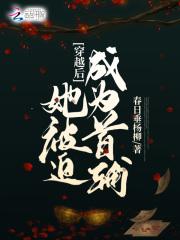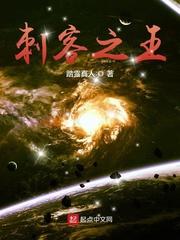笔趣阁>[综武侠]穿成过儿他姐之度步天下 > 427小人(第1页)
427小人(第1页)
风雨过后,晨光初透。南疆的天色如洗,云层裂开一线金芒,洒落在山寨屋檐上,像谁轻轻拂去尘灰。沈砚守在我身旁整整一夜,直到我的呼吸彻底停歇,心跳归于寂静,他才缓缓合上我的双眼,将那枚曾交还给男孩、又辗转由使者带回的青玉玉佩,轻轻放回我胸前。
他没有哭出声,只是跪在床前,一动不动,仿佛时间也随我一同凝固。
外头竹林沙沙作响,几只山雀飞落窗台,歪头望着屋内,似有所感。寨中长老闻讯赶来,围着竹屋默立良久。他们不懂朝廷文章,也不识破镜录为何物,但他们记得那个雨夜里,是谁用琴声止住了潭底哀嚎,是谁让祖辈遗忘的名字重新被唤起。
“她是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低声说,“来时无声,去时无痕,可吹过的地方,草木都活了。”
正午时分,山寨百姓自发集齐木材,在后山清出一片空地。他们不用铁钉,不刻碑文,只以古法搭起一座柴台,四角插着七支银丝缠绕的松枝??那是从井水中捞起的琴弦残片熔铸而成。沈砚亲手将我放入其中,手中紧攥着那本尚未装订的《破镜录》手稿。
火点燃的那一瞬,整座山谷忽然安静下来。
火焰升腾,映红了半边天空。就在此刻,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大雁塔顶铜铃无风自鸣;江南某书院的藏书阁里,一本尘封多年的《永昌实录》突然自行翻页,停在空白的末章;而敦煌石窟深处,壁画上的女子执琴身影竟微微颤动,眼角似有泪光滑落。
三日后,消息传遍天下。
“杨度死了。”
短短四字,却如惊雷滚过九州大地。有人痛哭失声,有人焚香祭拜,更多人默默取出纸笔,写下他们记得的事??哪怕只是童年一场暴雨、母亲一句叮咛、战场上一个战友的姓名。
记忆,开始反扑。
沈砚并未随使臣返京,而是留在南疆,住进我曾养病的小竹屋。每日清晨,他都会去那口涌出银丝的古井边打水,洗净笔砚,继续誊抄《破镜录》的副本。他知道,这本书不能只藏于宫廷档案,它必须流落民间,混入茶馆说书人的词话,成为孩童启蒙的读物,甚至刻上旅人歇脚的凉亭石柱。
一个月后,第一座“记忆碑亭”在渭南废村落成。正是当年我赠玉佩给男孩之处。那孩子带着全村人合力雕琢了一方石碑,正面刻着:“忠魂不泯”,背面则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不只是战死者的名讳,还有被大火吞噬的书生、因言获罪的谏官、默默饿死的灾民……每一个都是曾经被抹去的存在。
据说当夜月圆,碑前忽有琴音袅袅,无人弹奏,却清晰可闻。守碑老人跪地叩首,喃喃道:“她回来了。”
与此同时,归真会残党接连被捕。他们在各地暗设的“忘坛”被逐一掘出??那些埋在学宫地基下的青铜钟、藏在佛寺经柜里的迷香炉、甚至伪装成药铺配方的记忆蛊毒……尽数曝光。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参与其中的人并非恶徒,而是曾真心相信“遗忘才能太平”的士大夫。他们以为消除痛苦记忆便可换来盛世安宁,却不知真正的和平,始于直面黑暗的勇气。
新帝下诏,废除“涤魂令”,开放史馆禁书,并命礼部设立“记述司”,专责收集各地口述历史。更令人意外的是,他在太极殿前立下新规:每逢冬至,百官须共诵一段被遗忘的往事,不得重复,不得虚饰。
第一年冬至,宰相颤声念出:“永昌三年十一月初七,御史杨氏女,年十七,因父冤上书,杖毙于宫门外,尸身弃于乱葬岗。其母投井,其妹失踪……”
满朝皆泣。
而在终南山旧书院遗址,罗烬悄然现身。他已不再穿黑袍,也不再提复仇二字。他带来一箱箱从江湖各处搜集来的残卷,全是当年焚书运动中幸存的手稿。他在断墙残垣间建起一座露天学堂,招募流浪儿与孤女,教她们识字、背诗、讲述家族故事。
“你们不必做英雄。”他对孩子们说,“只要记得就够了。”
春去秋来,三年光阴流转。
沈砚走遍十五州郡,亲手督建了四十九座记忆碑亭。每到一处,总有人问他:“杨姑娘真的只是一个人吗?还是说,她是我们所有人心里不肯闭眼的那一部分?”
他从不回答,只递上一本《破镜录》。
某日行至江南水乡,正值梅雨时节。他在小镇客栈歇脚,听见楼上孩童朗读课文:
>“风无形,故不死;
>记忆无价,故不灭。
>杨度者,非一人之名,乃万民之心声也。”
他怔在廊下,久久不能言语。
当晚,他梦见我站在湖心小舟上,桐木琴横膝而置,银弦轻拨。四周雾气弥漫,但每一滴雨落下,都映出一个画面:某个少年在灯下抄录《破镜录》,某位老妪向孙儿讲述饥荒岁月,某位将军在阵前高呼牺牲者的名字……
“你看见了吗?”梦中的我回头微笑,“火种没断。”
醒来时,东方既白。他提笔写下最后一段跋文:
>**此书成后,我不再续。**
>
>**因它已不属于任何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