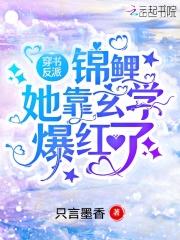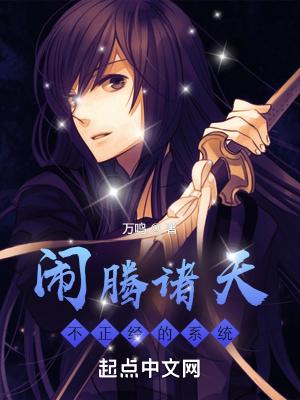笔趣阁>影视编辑器 > 第182章 杀倭(第3页)
第182章 杀倭(第3页)
或许以前的胡宗宪还会讲究一个权谋和手段,然而苏宁却是直接创了他们的祖坟。
万历三年的深秋,南京城的空气中已带上凛冽寒意,但浙直总督府内却弥漫着一种大战将至的炽热气氛。
经过数月周密侦查,结合“大明商会”遍布海外的商贸网络反馈,投降倭寇的供述以及AI系统对海量信息的分析比对。
苏宁终于锁定了困扰大明海疆数十年的毒瘤,倭寇主力及其最重要巢穴的准确位置。
竟然在琉球群岛以东,一座名为“八重山”的隐秘岛屿群。
苏宁并未急于行动。
他深知,跨海远征,非同小可,必须谋定而后动。
于是命令麾下绘制了精细的海图,标注了倭寇巢穴的地形、水文、防御工事以及可能的逃窜路线。
同时,他调集了经过台州之战检验,并进一步扩充的新式水师。。。。。。
包括已服役的“启明”号及另外两艘新建的蒸汽战舰,以及数十艘经过改装、装备辅助蒸汽明轮和新式火炮的大型战船。
陆师方面,则以经验丰富的戚家军旧部为骨干,配备了更多燧发鲁密铳和轻型野战炮,进行了高强度登陆作战演练。
准备就绪后,一道言辞恳切、证据翔实、战略清晰的《请剿倭寇根本疏》以六百里加急送往北京。
在奏疏中,苏宁首先陈述了确凿情报:“臣已得,倭寇巨酋王直之余党,并纠合诸岛浪人、海贼,盘踞于琉球以东之八重山诸岛,以此为巢,劫掠商旅,侵扰沿海,罪证确凿。”并附上了详细的侦查报告与海图副本。
继而,他分析了战略必要性:“以往,皆如扬汤止沸,其流窜之影,难毁其盘踞之根。今既知其巢穴,若不出重兵犁庭扫穴,则不过数年,彼必死灰复燃,海疆永无宁日。”
最后,他提出了具体的作战请求:“臣请旨,率浙直水陆精锐,渡海东征,直捣八重山贼巢。水师断其外援,陆师登陆清剿,务求全歼丑类,焚其营寨,毁其船只,以绝后患!此战若成,可保东南沿海数十年之太平!”
奏疏抵达京师,立刻在朝堂之上引发了比台州大捷时更为激烈的争论。
内阁值房内,几位大学士的意见泾渭分明。
以张居正为首的支持派态度审慎而坚定。
尤其是张居正仔细审阅了苏宁附上的海图和情报分析,目光锐利:“苏安邦行事,向来谋定后动。台州之捷,已证其能。今既有确凿巢穴,跨海征剿,正是一劳永逸之上策!若迟疑不决,待倭寇警觉转移,则失此良机,日后
剿抚,所费更巨!”
另一位支持此议的官员补充道:“元辅,苏总督麾下新式水师,船坚炮利,台州海战已显威力。陆师亦多百战之兵。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唯有根除祸源,方能彰显天朝威严,令四夷慑服!”
而以部分守旧勋贵和担心财政的官员为主的反对派却也有自己的理由。
“万万不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臣激烈反对,“跨海远征,劳师袭远,乃兵家大忌!茫茫大海,风涛难测,粮秣补给如何维系?若战事迁延,师老兵疲,岂非重蹈前元征日之覆辙?”
“耗费太巨!”户部侍郎立刻算起了经济账,“打造新式舰船已花费颇多,此番远征,粮饷、弹药、抚恤,又需多少银两?国库刚刚因‘一条鞭法”稍有起色,岂能再兴如此大规模战事?”
更有保守者忧心忡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苏总督已掌东南军政大权,若再赋予其跨海征伐之权,手握如此重兵,远在海外。。。。。。其势恐难制矣!”
这话虽未明说,但指向的正是对苏宁个人权势过度膨胀的深深忌惮。
争论持续数日,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年轻的万历皇帝端坐于龙椅之上,听着臣子们的辩论,小小的脸庞上露出与年龄不符的凝重。
他看向自己的老师兼首辅张居正,又看向那些激烈反对的老臣们。
张居正最终出列,做出了决定性的总结陈词,他面向御座,声音沉毅:“陛下,倭患乃大明心腹之疾,历代先帝皆欲除之而不得其法。今苏宁既侦得贼巢,又有新式水师可恃,此乃天赐良机!若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则倭患
永无平息之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老臣以为,当准苏宁所请,授予其临机专断之权,限期克敌!至于钱粮,可从海关税收及江南藩库中先行支应,待凯旋后,自有缴获补充,且海疆靖平,商路畅通,长远看,利大于弊!”
万历皇帝沉默片刻,他想起苏宁的种种功绩,也想起那“清廉”之名背后可能存在的深沉,更明白张先生决心已定。
最终,他稚嫩却清晰的声音在殿中响起:“准奏。着浙直总督苏宁,总督东南水陆兵马,跨海征剿八重山倭寇。一应事宜,许其便宜行事,务求全功!”
当皇帝的旨意和内阁的正式公文以最快速度送达南京时,苏宁早已准备就绪。
他站在“启明”号的舰桥上,望着江面上帆樯如林、蒸汽袅袅的庞大舰队,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传令!各舰按预定序列,拔锚起航!”
“目标,八重山!”
“此战,不留后患!”
雄浑的汽笛声划破长空,混合着风帆鼓荡的声响,庞大的大明舰队,承载着帝国的意志与苏宁的雄心,缓缓驶出长江口,劈波斩浪,向着东方那片未知的,隐藏着帝国宿敌的海域,义无反顾地进发。
一场决定东海未来数十年格局的远征,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