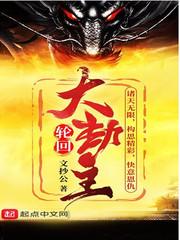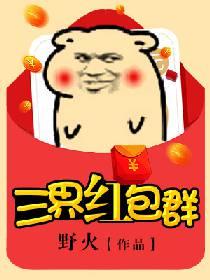笔趣阁>国潮1980 > 第一千六百四十九章 泥石俱下(第1页)
第一千六百四十九章 泥石俱下(第1页)
泥石俱下。
这几个字,对于当下日本极度萎靡的经济局面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诠释。
1990年11月中旬,尽管日本相扑界,有史以来最帅的横纲选手千代富士,收获其职业生涯总计第1000场胜利。
。。。
艾米丽看着女儿稚嫩的笔触,心头一颤。那盏歪歪扭扭的红灯笼,像是从遥远东方飘来的光,轻轻落在纸页上,也落进了她心里。她把相册合上,抱起孩子走向窗边。窗外是托斯卡纳丘陵绵延的橄榄树林,雨后初晴,阳光斜照在石板路上,泛着湿润的光泽。她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踏上北京南锣鼓巷的那个清晨??雪还没化尽,青砖灰瓦间冒着热气,一个穿棉袄的女人站在院门口,朝她伸出手:“欢迎来到‘守常居’。”
那时她只是个背着相机、满脑子浪漫幻想的意大利留学生,以为来中国是为了拍一组“异域风情”的毕业作品。可当她跟着米晓卉走进正在修缮的“益商堂”,看见几个年轻人跪在地上一片片拼接脱落的雕花木窗时,她才明白,这不是旅游摄影,而是一场沉默的抵抗。
“妈妈,我们也能画灯笼吗?”女儿的声音打断了回忆。
“当然。”艾米丽微笑,“而且我们可以寄给中国的朋友们。”
她取出水彩颜料,在一张宣纸上慢慢勾勒。红纸、金穗、竹骨、蜡烛……每一笔都带着记忆的温度。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自三年前她在佛罗伦萨办完《京灯计划》影像展后,便陆续有欧洲学校联系她,希望引进“晨读角”模式。起初只是几所华文学校尝试每周诵读《三字经》,后来连本地小学也开始用中文课教唐诗,并配上古琴伴奏。最让她意外的是,去年冬天,罗马一所公立中学竟自发组织学生募捐,为云南一座即将倒塌的书院筹集修缮资金。
“原来灯火真的会传递。”她在一次讲座中说,“它不靠口号,也不靠强制,只靠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眼里的光,然后决定自己也要点亮一盏。”
与此同时,北京的春天正悄然复苏。
四月的南锣鼓巷,玉兰花开得正盛,花瓣随风飘进“守常居”的天井,落在陈知微摊开的手绘图纸上。十年过去,那个曾抱着摄像机冻红脸蛋的女孩,如今已是“京灯计划”建筑修复组的负责人。她手中的这份图纸,属于第十五座待修院落??位于西城区的一处清代私塾遗址,当地人称“墨香斋”。
据地方志记载,此处原为一位退隐御史创办的义学,专收贫寒子弟。鼎盛时有学子百余人,夜间灯火通明,故得名“夜读庐”。民国年间逐渐荒废,建国后被划为粮库,八十年代又改建为职工宿舍楼,仅剩半堵山墙和一段残破影壁得以留存。
“难点在于地基沉降严重,周边又有新建住宅楼,施工空间极小。”陈知微指着剖面图对团队讲解,“但我们发现,地下可能还埋藏着原始讲堂的地坪结构。如果能确认位置,或许可以原址复建。”
米晓卉站在她身旁,听得认真。这些年,她虽不再事事亲力亲为,却依旧坚持参加每一次踏勘与评审会。她的头发已染上霜色,眼神却比从前更加清明。
“你们有没有问过附近老人?”她突然开口。
众人一愣。
“十年前修明伦堂时,我们走访了三百多户人家,才找到周老先生这样的亲历者。现在这片区域虽然拆迁过半,但总还有些老住户没搬走。也许他们记得些什么。”
当晚,陈知微带两名志愿者提着点心上门拜访几位留守居民。其中一位七十八岁的张奶奶听说要修“墨香斋”,竟激动得落下泪来:“我爹就是那儿念的书!他说每天五更就得起床,背着手站在院子里等先生开门。谁要是偷懒,就得抄一百遍《千字文》。可那时候的孩子,个个识文断字,走出去都有体面。”
她颤巍巍从柜子里翻出一本泛黄的小册子:“这是我爹留下的日记,你们拿去看吧。里面有他画的学堂平面图。”
陈知微接过本子,指尖微微发抖。翻开第一页,一行工整小楷跃入眼帘:“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三,入夜读庐。先生姓李,讳怀瑾,授《论语?学而篇》。”
后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课程内容、同学姓名、考试成绩,甚至还有一次偷看话本被罚站的趣事。而在最后一页,赫然是一幅手绘学堂布局图??门厅、讲堂、厢房、藏书阁、后花园,标注清晰,比例准确。
“这是文物级资料!”回程路上,年轻志愿者几乎喊出来。
陈知微却久久未语。她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城市光影,忽然觉得,自己手中捧着的不仅是一本日记,更是一个时代的呼吸。
一周后,“墨香斋”修复方案正式立项。基于张爷爷日记中的图纸,结合考古勘探结果,团队决定采用“双层空间”设计:地面以上按原貌重建传统院落,供公众参观与文化活动;地下则保留现存地基遗迹,打造沉浸式展览区,通过全息投影还原清末课堂场景。
工程启动当天,米晓卉亲自到场奠基。她没有讲话,只是默默将那本日记放入一个特制铜盒,埋入新地基之下。盒内还有一封信,是她写给未来某位少年的:
“亲爱的孩子:
当你读到这封信时,也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但请相信,此刻我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心中充满希望。
我不知道你生活在哪一年,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模样。但我愿意赌一把??赌你会在乎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会为一句‘学而时习之’动容,会在某个清晨走进这座院子,感受到百年前书声琅琅的余温。
如果你做到了,请替我再点一盏灯。
因为只要灯还在亮,就说明我们没有输。”
雨水顺着屋檐滴落,敲打着青石台阶。工地旁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几个小学生正围坐在志愿者身边,听他们讲述“夜读庐”的故事。一个男孩举手问:“老师,那时候的学生也会犯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