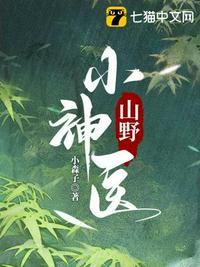笔趣阁>红楼之黛玉长嫂 > 192第 192 章(第2页)
192第 192 章(第2页)
与此同时,周砚之奉命巡视边防归来,途经江南,见昔日织造局废墟之上,竟建起一座大型女子工坊,专事丝绸印染与机械织造。厂主竟是当年受害织户之女,如今已成为技术骨干,带领三百余名女工自食其力。她告诉周砚之:“林大人说,不能让悲剧重演。所以我们自己办厂,自己定价,自己送货。现在我们的‘黛玉绸’销往西域,比官办局子的货还贵两成!”
周砚之闻言久久伫立,归京后径直登门拜访黛玉。两人相对而坐,茶烟袅袅,他忽然开口:“你可知天下人如何议论你?”
“无非说我牝鸡司晨,离经叛道罢了。”她淡笑。
“可也有人说,你是月下海棠,寒而不凋;是破晓孤星,暗中引路。”他凝视她,“这些年,你点亮了太多人的路。可你自己呢?有没有想过,该为自己留一盏灯?”
黛玉怔住。窗外暮色渐浓,檐角铜铃轻响。她望着手中半杯冷茶,忽觉胸口一阵酸涩。这些年,她日夜操劳,未曾婚嫁,没有子女,甚至连一顿安稳饭都少有。梦里常回潇湘馆,听见母亲唤她“玉儿”,醒来却是孤灯残影。
良久,她低声道:“我若贪图安逸,便不会走这条路。世人总以为女人该择一人终老,可我觉得,有些使命,比姻缘更重要。”
周砚之沉默片刻,缓缓从袖中取出一枚玉佩,递给她:“这是我母遗留之物,说是传给儿媳。我一直未娶,就是在等一个人??一个值得让我放下刀剑,甘愿守候的人。”
黛玉望着那玉,指尖微颤,却没有接。
“砚之……”她声音极轻,“我不是不愿,而是不能。我这一生,注定属于千千万万个看不见光的人。若我转身走入庭院深深,谁来替她们说话?谁来为她们抗争?”
他苦笑:“所以你宁愿做万人敬仰的‘昭德郡君’,也不肯做周家的妻子?”
“不是不肯,是不敢。”她终于抬头,眼中含泪,“我怕有一天,当我选择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时候,这个世界又退回黑暗。我不敢赌。”
屋内陷入长久寂静。远处传来更鼓声,一下,又一下。
次日清晨,周砚之离开林府,再未提及婚事。但他每月都会送来一批新收养的孤女名单,请黛玉安排入学;每逢年节,必差人送上药材补品,附笺上只写二字:“保重。”
而黛玉依旧每日黎明即起,批阅奏章,接见申诉,巡视学堂。她开始着手推动“婚姻自主法”,严禁父母包办、买卖童养媳,规定男女订婚须双方亲笔画押,离婚亦可由女方提出。此举再度引发士林激烈攻讦,有腐儒撰文骂她是“灭伦祸水”,甚至有人匿名投毒,幸被紫绡察觉,及时换茶具逃过一劫。
但她毫不退缩。在一次公开讲学中,她面对数百学子直言:“婚姻不该是交易,而是选择。一个女人有权决定嫁给谁,也有权决定不嫁。她可以爱一个人,也可以不爱;可以生儿育女,也可以独身终老。这不是悖逆礼教,而是回归人性。”
台下掌声雷动。一名年轻女学生站起来喊道:“先生!我要写一本书,叫《女人的一百种活法》!”
黛玉笑了,那是近年来最真切的笑容。
冬雪再临,长安城外新建了一座“女子英烈祠”,供奉十年来为改革牺牲的女官、教师、医者与战士。其中一块碑上刻着两个名字:一个是伪装流民死于饥荒的监察院新人,另一个是为保护学生而被暴徒杀害的乡村女教习。
黛玉亲往祭拜,献上一束白梅。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是神明,无法救下每一个人。但只要有人记得她们的名字,她们就从未真正死去。”
这一年除夕,皇帝破例允许她参与宫廷家宴。席间皇子提问:“姑母(时称)为何终生不嫁?”
她举杯微笑:“因为我早已嫁给了这个国家,嫁给了千万姐妹的命运。而我的孩子,是每一个能昂首走路的女人,是每一双学会写字的手,是每一声敢于说‘不’的呐喊。”
四海升平,万象更新。第二年春天,第一批由女子担任的知县正式赴任,她们穿着官服,骑着骏马,穿过欢呼的人群,走进曾经禁止女性踏入的县衙大门。百姓燃放鞭炮,孩童追逐喊道:“青天奶奶来了!”
多年后,当史官撰写《大汉昭德录》时,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林氏黛玉,出身诗礼,志存高远。掌监察而肃纲纪,兴女学而启民智,废贱籍而正人伦,通西域而化干戈。虽处闺阁之身,行宰辅之事;未居帝后之位,成不世之功。天下女子因之挺脊,弱者得其所归,愚者开其蒙昧。故曰:一代风骨,千秋典范。”
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紫绡悄悄将黛玉晚年所用的一方砚台藏起,背面刻着一行极小的字,是她亲笔所书:
“若时光倒流,我仍会选择这条路??哪怕孤独终老,也要让后来者,走得更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