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激荡1979! > 第500章 两个黄金二百五(第1页)
第500章 两个黄金二百五(第1页)
“是啊,房子的合同已经签了。”
车上,阿敏跟魏明说起了买房的事情,现在还觉得有点刺激,这是她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而且妈妈把房子挂在了她的名下。
“花了多少钱啊?”魏明问。
说起这个阿敏。。。
赵桂芳收到邮件那天,正坐在炕头缝一双棉鞋。窗外是漠河零下三十七度的寒夜,风刮在木屋外墙上像刀子划过铁皮。她戴着老花镜,手指冻得发僵,点开手机屏幕时还沾了点浆糊??那是她刚补好的手套漏出的棉花粘上的。
看完信,她没哭,只是把手机轻轻搁在膝上,望向墙角那张泛黄的黑白照:1976年春,她站在气象塔前,穿着臃肿的棉袄,辫子扎得紧紧的,笑得像个刚打赢一场仗的士兵。
“林子绿了……”她喃喃道,“真好。”
她想起五十年前那个雪夜里,站长拍着她的肩说:“小赵啊,你一个姑娘家,何必来这儿?北纬53度,风吹得能削人皮。”她说:“别人能待,我就能待。我不怕冷,只怕看不见明天的日出。”
如今,她看见了。不止一日,而是成千上万个日出,在她一笔一划抄录的数据中悄然升起;在后来那些卫星云图精准预报的背后静静燃烧;在孩子们课本里写着“中国最北气象站”这几个字时轻轻闪动。
第二天清晨,她拄着拐杖走到院子中央,抬头看了看天。天边一抹淡红,像是谁用指尖蘸了朱砂,在灰蓝的幕布上轻轻抹了一道。她忽然转身回屋,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全是几十年攒下的记录本??纸页发脆,边角卷曲,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着温度、气压、风速、降雪量。她在最后一本扉页上写道:
>“交给孟波同志。这些不是废纸,是一个女人活过的证据。”
她把盒子包进油布,又用麻绳捆结实,托村里的邮递员寄出去。邮递员临走前问:“大娘,这东西重不重?”
她笑了笑:“不重。可它撑得起一片天。”
与此同时,上海郊区的一间老房子里,陈红梅正跪在地上整理母亲遗物。自从那封信寄出后,她像是终于打开了心里一道锈死的门。她不再回避母亲的名字,反而开始主动打听、追问、寻找。她联系上了三位曾与母亲共事的老工程师,其中一位住在成都,已卧床两年,说话断续,却坚持让女儿代笔写了一封长信:
>“你妈妈是我们中最聪明的一个。1971年那次引信误触警报,所有人都慌了,只有她蹲下来听声音。她说‘不是引爆倒计时,是继电器接触不良’,然后拆开外壳,用镊子夹出一根松动的铜丝。机器修好了,但她被政工科批评‘擅自操作,无视规程’。
>
>可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厂长偷偷送来一碗红糖鸡蛋,放在她门口。没人知道是谁送的,但我们都知道是他。”
陈红梅读到这里,眼泪砸在纸上,晕开了墨迹。她突然明白,母亲一生所受的委屈,并非无人看见,而是太多人选择了沉默地共情??就像她现在做的这样。
她决定去一趟绵阳。不只是为了祭拜母亲,更是要走进那座早已废弃的厂区,亲手触摸那些冰冷的墙体和生锈的轨道。她带上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母亲年轻时的笑容,另一张是轮椅上的背影。
抵达那天,正逢春雨。细雨如针,刺在脸上微疼。厂区大门依旧封着,铁链锈蚀断裂,藤蔓缠绕如网。她拨开枝叶,一步步踩着湿滑的石阶往里走。杂草齐腰,碎玻璃散落一地,几栋厂房塌了屋顶,像巨兽残骸。
她在主控楼前停下脚步。门框上方还能辨认出“安全第一生产为国”的标语,油漆剥落,字迹斑驳。她掏出那张年轻的照片,贴在墙上,低声说:“妈,我带你回来了。”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声。一位白发老人撑着伞走来,穿着旧式工装裤,脚蹬胶靴。“你是……陈工的女儿?”他声音沙哑,“我叫刘建国,以前和你妈一个班组。”
两人站在雨中聊了近两个小时。老人回忆起很多事:陈玉兰最爱喝苦丁茶,说能提神;她总随身带着一把小锉刀,用来打磨引信零件;她咳嗽厉害时也不请假,只把自己关在通风间里工作,怕传染别人。
“你知道她为什么从不说功劳吗?”老人忽然问。
陈红梅摇头。
“因为她觉得,说出来就是对牺牲者的不敬。1973年那次排爆,其实有两个人申请进去??另一个是男同事,比她早三年进厂。领导选了她,是因为她个子小,能钻进狭窄通道。那人后来调走了,再没见过。你妈一直记着这事,说‘是我抢了他的命’。”
陈红梅怔住了。原来母亲的沉默,不只是因为体制压抑,更源于一种深不见底的责任感??她把每一次幸存,都当作对他人生命周期的侵占。
“所以她宁愿背负‘冷漠’‘古怪’的评价,也不愿被人称颂?”
“是啊。”老人点头,“她说:‘荣誉是死人的陪葬品,活着的人,只管做事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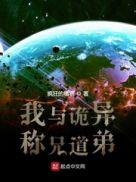
![总有偏执狂盯着我[快穿]](/img/3097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