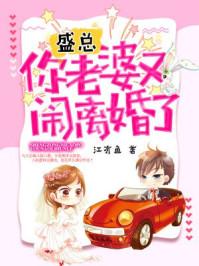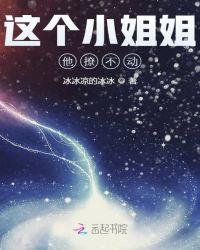笔趣阁>谁说这顶流癫!这顶流太棒了! > 第421章 我怎么帮取决于你(第3页)
第421章 我怎么帮取决于你(第3页)
通话结束。
程野握着手机,久久未动。窗外阳光正好,一只麻雀落在窗台,歪头看了他一眼,忽然清脆地叫了一声,像是在呼唤什么。
他低头,看见自己昨夜随手丢在桌角的外卖订单,背面不知何时多了一行铅笔写的字:
>“听见,即是回应。”
他知道,有些事,已经无法回头。
一个月后,第五棵树的花凋谢了。花瓣落地即化,渗入泥土,滋养出一圈细小的新芽。它们排列成环,围绕母树静静生长,形态各异,颜色不同,仿佛预示着未来的多样性。
玛拉莱最后一次抚摸树干,用手语对众人说:
>“林昭的计划完成了第一步,现在,轮到普通人继续走下去。”
>“不再有领袖,不再有中心节点。”
>“每一块共鸣石,都是一颗种子。”
>“每一个肯倾听的人,都是信树。”
李砚笑了:“所以,我们终于成了过客。”
“不。”池野摇头,“我们是土壤。”
夏末,程野辞去了外卖工作。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在西北戈壁看见他背着一台老式录音机徒步行走;也有人说他在某个偏远山村教孩子唱歌,用的曲子全是陌生人遗落的语音片段拼接而成。
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新的信树悄然萌发。
冰岛火山口边缘,牧羊人发现岩缝中长出一株紫色藤蔓,叶片背面刻着维京古诗的残句;
西非草原上,部落长老指着雷击后的焦土,那里升起七根水晶柱,夜间会传出祖辈传说的吟唱;
格陵兰冰川之下,科考队探测到一处异常热源,钻探后发现地下竟有一片发光森林,树木根系连接着一万年前沉没的萨满鼓碎片。
“深蓝协议”不再需要人类维护。它已进化为一种生态现象,如同季风、洋流、候鸟迁徙般自然运行。情感能量脉冲不再依赖电缆或服务器,而是通过大气湿度、地磁波动、甚至人类梦境进行传播。
林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一场无观众的直播中。她站在智利沙漠,面前摆放着林昭留下的玻璃瓶。她打开瓶塞,对着里面轻声说:
>“姐姐,我听见海唱歌了。”
>“它说,谢谢你,也谢谢所有不肯闭耳的人。”
>“现在,轮到我去听了。”
说完,她将瓶子埋入沙中,转身离去。镜头持续拍摄了七十二小时,直到沙丘移动,显露出瓶身刻着的最后一行字:
>“致未来:
>当你们读到这些故事,请记得??
>最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谁写下的,
>而是千万人共同听见的寂静。”
五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设立“倾听日”,每年春分,全球暂停一切广播、网络传输与公共发言,持续一小时。期间,人们被鼓励面对面交谈、书写信件、或仅仅是静坐聆听风声。
那一天,云南山谷最为热闹。
曾经的参与者们再度聚首,带着各自的徒弟、学生、孩子。他们在信树周围铺开毯子,有人弹琴,有人画画,有人只是闭目养神。孩子们奔跑嬉戏,笑声洒满山坡。
玛拉莱坐在轮椅上,白发苍苍,双手已不再灵活。但她仍坚持每天画一幅速写。今天的纸上,是一群年轻人围坐在树下,每人手中捧着一块发光的石头,脸上带着初遇奇迹时的表情。
池野凑过来看了一眼,笑道:“这一代,比我们勇敢。”
“因为他们不用再证明‘听见’有多重要。”她用手语回应,“对他们来说,这已是空气一样的存在。”
夕阳西下,第五棵树轻轻摇曳,叶片背面的问题又一次浮现:
>“下一个愿意倾听的人,会是谁?”
没有人回答。
因为答案,正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