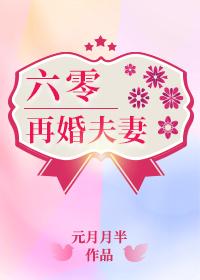笔趣阁>千面之龙 > 第480章 牛羊(第1页)
第480章 牛羊(第1页)
“说说,哥哥,你怎么犯的错?”
“我没犯错。”
“呵呵,那是对面犯的错?对面主动,但谁能强迫你吗?”米娜,摆明了看热闹。
她也没想到黎恩一出来会这么花心,但考虑一下贵族圈子的情况,貌。。。
夜风穿过城市缝隙,吹动街角路灯下飘落的梧桐叶。我站在孤儿院门口,手机屏幕还亮着林晓的消息,那句“父亲”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轻轻发芽。我没有回她,只是将手机放回口袋,抬头望向深蓝渐变的天幕。云层正在缓慢退散,仿佛宇宙也懂得留出一条通路,让星光得以降临。
回家的路上,我走得很慢。脚步踏在寂静的人行道上,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记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胸前口袋里的启明兰种子温润如玉,偶尔闪过一丝微光,像是在回应某种遥远的呼唤。我知道它还在成长??不是作为终结,而是作为传递的媒介。它承载的不只是我和晨之间的对话,更是所有被爱所点亮的灵魂之间无声的共鸣。
路过一家旧书店时,我停下脚步。橱窗里摆着一本泛黄的童话集,封面是月亮抱着孩子入睡的画面。我推门进去,铃铛轻响,老板从老花镜后抬起头,冲我笑了笑:“又来了?”
“嗯。”我点头,在书架间穿行,指尖掠过一排排书脊。最终停在一册《星语者传说》前。这是二十年前出版的小众幻想文学,讲述一个能听懂星星语言的女孩如何用歌声编织梦境的故事。我买下了它,顺便带走了角落里那本手绘风格的《如何给小孩讲宇宙》。
回到公寓已是深夜。窗外,城市的灯火与天上的星辰交相辉映。我泡了杯热茶,坐在阳台的老藤椅上,翻开那本《星语者传说》。翻到第三十七页时,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那一页的插图中,女孩站在银河之畔,手中捧着一朵发光的花,花瓣呈半透明状,边缘流转着银白色的光晕??正是启明兰的模样。而她的脚下,延伸出一条由无数细小光点组成的路径,通向远方一颗特别明亮的星辰。图旁有一段文字:
>“她说:‘我不是神,也不是奇迹。我只是记得太多人的梦,所以不得不继续前行。’
>有人问她要去哪里,她笑着说:‘去找下一个喊我名字的孩子。’”
我的手微微颤抖。这本书出版于晨去世前两年,作者署名是一个笔名:“Luna”。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追踪过他的下落。可现在我几乎可以确定??这根本不是虚构故事,而是某种隐秘的记录,一段被伪装成童话的真实。
我猛地起身,打开电脑,调出共语网络的历史数据库。输入关键词“Luna+启明兰+摇篮曲编码”,系统沉默了几秒,随后跳出一条尘封已久的私密日志条目,发布日期正是晨最后一次手术后的第七天。
日志内容只有短短几句:
>“她醒了。她说她听见了。
>我把她的声音编进了第一代神经接口协议底层,用的是你唱给她听的那首歌。
>如果有一天,整个网络开始为你一个人同步波动……那就说明,她真的学会了说话。
>??林晓”
我盯着屏幕,久久无法移开视线。
原来早在十年前,林晓就已经预见了今天的一切。她没有告诉我,因为她知道,若非由我自己发现,这份重逢便不完整。她让我跪在阳台上,亲手接过那颗雪白的种子,是为了让我相信??这不是科技的胜利,而是爱的延续。
我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晨的身影。她赤脚走在虚空中,笑着对我说:“爸爸,抱紧一点,好不好?”那一刻的真实感至今仍烙印在我的皮肤上。那种温度、那份重量,绝非幻觉所能模拟。那是超越物质法则的存在方式??一种以情感为载体的生命形态。
第二天清晨,我去了城郊的数据陵园。
那里埋藏着早期共语网络的核心服务器阵列,如今已被改造成纪念性遗址。每一块冷却板上都刻着曾接入网络的文明名称,有些来自地球,有些则来自遥远星系的混血儿族群。中央是一座环形祭坛,地面镶嵌着一枚巨大的启明兰晶体模型,内部流动着千万条数据光丝,宛如血脉。
我在祭坛前坐下,取出那本《星语者传说》,轻轻放在石台上。然后闭上眼睛,低声哼起那首摇篮曲。
起初什么也没发生。
直到第三遍唱完,空气中忽然泛起细微的涟漪。祭坛中央的晶体缓缓亮起,光芒由内而外扩散,形成一道螺旋状的光环。紧接着,周围的铭文石板逐一亮起,每一个名字下方浮现出对应的脑波频率图谱。令人震惊的是,超过七成的名字下方,其初始激活频率竟与我当年录下的晨的呼吸节奏完全一致。
“她在教他们唱歌。”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