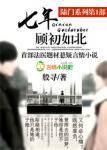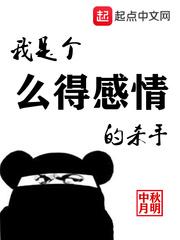笔趣阁>挟明 > 第七四五章 柳二爷陷阵敢死爆神威(第1页)
第七四五章 柳二爷陷阵敢死爆神威(第1页)
杭州北关城楼上,管事的守备管带马百总话里藏锋,有意扯去贺喜之事,欲凭此唬瞒,来探柳二真身。
对相关前下的柳哲成眸间亦有紧转,愕然骇色藏心头,急是琢磨嘟囔。
也幸亏了是自己乃督军亲随,其大婚。。。
马车自江宁启程,沿官道西行。朱允熙未带仪仗,只着素袍,随行仅两名内侍、四名莲卫改装的护卫。他执意轻装简从,说是不愿惊扰百姓,实则心中明白:此去云南,非为巡狩,而是赴一场生死之约。
沿途所见,尽是新政初行后的痕迹。昔日荒芜田亩如今翻土耕种,村口竖起“清田使”立碑,上书丈量结果与赋税定额;驿站旁张贴《科举革新榜》,乡民围聚议论,有老翁拄杖叹息:“我儿若早生十年,何至于困守田垄?”也有少年跃跃欲试,打听何时开考算术一科。
朱允熙在车内静观,不发一言。每当车队停歇,他便下车步行片刻,与农夫交谈,问收成、问徭役、问新政推行是否顺畅。起初百姓惶恐跪拜,经他反复安抚,才敢开口直言。有人抱怨清田使偏袒豪族,暗中少报田亩;也有人说匠籍开脱令虽好,但地方官仍视工匠为贱役,不予授职。朱允熙一一记下,命随行文书登记造册,回京后交由柳含烟彻查。
行至江西境内,天降暴雨,山路泥泞难行。车队被困于一座破庙三日。夜深人静,朱允熙独坐灯下,取出袖中那页残破的《田制考》抄本??并非太庙封存的那一册,而是他幼年时桂王亲授的原本,多年来始终贴身携带。纸页已泛褐,边角卷曲,批注却依旧清晰可辨。他指尖抚过一行小字:“民无恒产,则心无恒安;赋不均平,则国必倾危。”这是桂王当年朱笔所书,墨色沉厚如血。
他闭目默诵,仿佛又听见那位温雅而坚毅的叔父在耳畔低语:“熙儿,治天下不在权谋,而在知民心、顺民情。”
睁开眼时,烛火跳动,映出墙上影子,竟似两人并立。
第四日清晨雨歇,车队继续前行。翻越五岭之后,进入滇东地界。山势陡峻,云雾缭绕,鸡足山遥遥可见,形如金鸡独立,佛光隐现于林梢之上。陈阿保所在的村落藏于半山腰,原是桂王府旧仆聚居之地,名为“归心庄”。百年前曾香火鼎盛,如今只剩断垣残壁,唯有一株千年桂花树仍挺立院中,每至秋日花开,香气弥漫整座山谷。
庄中老人见马车到来,纷纷扶杖而出。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妪颤声唤道:“可是……可是熙少爷回来了?”
朱允熙下车上前,躬身行礼:“孙婆婆,是我。”
老妪泪如泉涌,拉着他的手不肯松开:“你终于回来了……阿保天天念你,说若能再见你一面,死也瞑目。可这一个月来,他连床都起不得了,话也说不清了……”
众人引他入屋。茅草覆顶,土墙斑驳,陈阿保躺在竹榻上,瘦骨嶙峋,双目紧闭,呼吸微弱。床头供着一块褪色红绸,里面包裹的正是当年那枚青铜铃铛,铃舌已断,却仍被老人每日擦拭。
朱允熙轻轻握住他的手,低声唤道:“阿保爷爷,我来了。”
老人眼皮微微颤动,良久,缓缓睁眼。浑浊的目光在朱允熙脸上停留片刻,忽然剧烈抽搐,嘴唇哆嗦着,想说话却发不出声。
“别急,我在。”朱允熙将耳朵贴近,听他气若游丝地吐出几个字:
“……盒子……还……完整吗?”
“完整。”朱允熙哽咽,“《田制考》已归太庙,收养文书焚于烛火。您交代的事,我都做了。”
陈阿保嘴角艰难扬起一丝笑意,又断续道:“……王妃……临终前……说……‘新政不成,魂不得安’……如今……可……成了?”
朱允熙点头:“丈田令行于十四省,清田使报称新增耕地三千六百万亩;科举已改,首试报名者逾十万;匠籍除名十二万,皆授工牌,可自由择业。江南百姓分田免赋,江北战后重建,亦按功授田。孙可望虽诈降未果,然朱氏内乱,西北暂稳。郑经舟控海断粮,李承勋退守山东,江淮再无大战。”
每说一句,陈阿保的眼中便多一分光亮。待说完,老人竟奇迹般抬起右手,颤抖着指向屋角那只铜盒??正是当年送至江宁的那只,不知何时已被送回。
朱允熙起身取来,打开一看,除《田制考》外,底层另有一封密函,火漆完好,封皮写着:“待吾儿亲启”。
他心头一震,正欲拆阅,却被陈阿保用尽力气抓住手腕,摇头示意不可。
“……不是现在……”他喘息道,“等……天下太平……再看……否则……心会乱……”
朱允熙凝视着他,重重点头:“好,我答应您。”
陈阿保终于放松下来,长舒一口气,眼神渐渐涣散。他最后望了一眼窗外那株桂花树,轻声道:“桂花……开了啊……”
话音落处,手垂下,气息全无。
屋内一片寂静。众人跪地垂首,唯有风穿窗而入,吹动桌上黄纸,沙沙作响。
朱允熙久久不动,伏在榻前,将老人的手轻轻合拢于胸前,然后取出随身佩刀,割下一缕青丝,放入铜盒之中,盖上红绸。
“从此以后,我不再是孤身一人。”他低声说,“你们都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