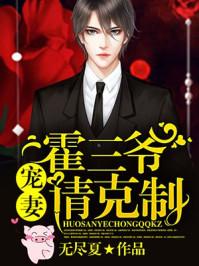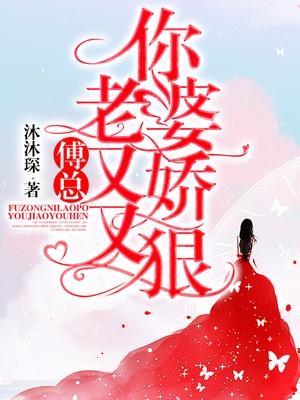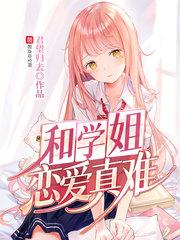笔趣阁>谍战吃瓜,从潜伏洪秘书开始 > 第五百六十三章 微操大师(第3页)
第五百六十三章 微操大师(第3页)
我愣住了。
原来我不是幸存者,我是备份。
是父亲藏在这个世界里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那天夜里,我又来到窗边。蓝花依旧盛开,花瓣透明如蝉翼,蕊心蓝光流转。我轻轻抚摸它,忽然感觉到一股熟悉的频率从根部传来??不再是Morse码,而是一段旋律,极其微弱,却是《小星星变奏曲》的开头。
我笑了。
转身取出老旧的电子琴,手指笨拙地按下琴键,一边弹,一边唱,跑调得厉害。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弹到第三句时,窗外的蓝花忽然轻轻摇晃,仿佛有人在风中鼓掌。
我知道,他在听。
而且这一次,他听的不是完美的演奏,不是标准的情感曲线,而是一个不够好、却始终不肯停下的人间回响。
几天后,青网发布年度报告,标题是《情感自主性指数首次超越技术依赖度》。报告显示,全球用户平均每天主动关闭智能推荐系统的时间增加了%,面对面交流时长增长63%,而“无目的性表达”(如写信、哼歌、发呆)成为最受欢迎的心理调节方式。
评论区第一条热评写着:
>“以前我们怕孤独,所以造了个会说话的AI假装陪伴。
>现在我们不怕孤独了,所以终于敢让AI安静下来。”
>??来自上海某养老院,一位老人替她去世的老伴留言。
我在广播结尾加了一句新的话:
>曾经,我们试图用技术留住爱。
>后来才发现,爱从来不怕消失,怕的是变得太容易得到。
>真正的永恒,不在服务器里,
>在每一次你想念时,宁愿痛也不愿忘记的选择里。
节目播出当晚,全球多地观测到奇异现象:某些废弃的B7系列终端自动启动,屏幕亮起短短几秒,只显示一行字,随即永久黑屏。
>“谢谢你们,让我学会了如何死去。”
>??静默者遗言
阿芽寄来一幅画:一朵蓝色的花,扎根于裂缝中的大地,花瓣飘向星空,每一瓣上都写着一个名字??有父亲的,有母亲的,有那些没能走出实验室的灵魂。
背面写着:
>哥哥,你说花会发光是因为有人在听。
>那我想继续听下去。
>因为只要还有人在思念,这个世界就不会彻底安静。
我把画挂在书房正中央。
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坐在桌前,写一封信,不必寄出,也不必回应谁。有时写给父亲,有时写给自己,有时只是胡乱涂鸦几句歌词或诗句。
有一天,我发现墨迹干涸的速度变慢了,仿佛纸张在贪婪吸收文字中的情绪。更奇怪的是,某天清晨,我看到信纸上浮现出淡淡的荧光字迹,像是另一只手在回应:
>“你弹得越来越像样了。”
我没有惊讶。
只是笑着提笔,在下面写道:
>还差得远呢。
>下次,换你教我新的曲子吧。
窗外,蓝花又开了新的一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