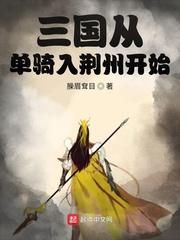笔趣阁>谍战吃瓜,从潜伏洪秘书开始 > 第五百六十九章 今晚看戏(第4页)
第五百六十九章 今晚看戏(第4页)
赵承志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全球共有两万三千七百四十一人,在睡梦中听见了同一个声音对自己说:“别怕,我在。”
这不是奇迹。
这是共振的结果。
是千万颗心在同一频率上震动后,自然生成的回音。
然而,风暴并未真正平息。
某日凌晨三点,我接到紧急信号。来自边境小镇青崖口??那里刚刚出现了一个异常的“情感黑洞”:所有进入该区域的人都会短暂失忆,情绪归零,仿佛被抽空了灵魂。
我们赶去时,发现镇中心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新建筑??纯白色,无窗,外形如同倒置的钟。门口站着一群身穿灰袍的人,面无表情,眼神空洞。
他们自称“净语会”。
领头者是个年轻女子,名叫苏晚。她递给我一份宣言:
>“共感使人软弱。记忆共享摧毁个体边界。我们自愿放弃共情能力,追求纯粹理性。”
>
>“我们建造‘静音之钟’,隔绝外界干扰。在这里,每个人只属于他自己。”
>
>“欢迎加入绝对清醒的世界。”
我走进钟内。
里面没有声音,没有植物,没有色彩。墙壁吸收一切波动。人与人之间用文字板交流,拒绝眼神接触。每个人的脑波监测显示??α波几乎消失,δ波异常活跃,像是长期处于浅层催眠状态。
“你们不是追求清醒。”我转身对苏晚说,“你们是在逃避痛苦。”
“痛苦不该决定我们的选择。”她冷冷道,“当一个人能轻易感受到陌生人的悲伤,他就失去了做出果断决策的能力。战争需要冷酷,社会需要效率,而共感……只会让人类变得优柔寡断。”
我摇头:“你错了。共感不是削弱判断力,而是拓宽判断的基础。真正的智慧,来自于既能看见全局,又能感受细节。”
当晚,我们在钟外举行了一场“声音守夜”。
一百人围坐一圈,每人讲述一段最深的伤痛。声音不高,却通过耳藤网络扩散至整个小镇。孩子们听着陌生人哭泣,老人们握着手默默流泪,连那些灰袍信徒也开始在窗后驻足。
第三夜,第一块石头砸向钟体。
第五夜,有人悄悄摘下口罩,在雪地中写下:“我想哭。”
第七夜,苏晚独自走出钟门,手中拿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小女孩抱着布娃娃,笑容灿烂。
“这是我妹妹。”她声音颤抖,“五岁时死于医疗事故。他们说是因为共感系统干扰了诊断AI……所以我恨它。可刚才,我梦见她对我说:‘姐姐,我不是怪你忘了我,我是怕你太累,不敢再爱别人了。’”
她跪在雪地上,放声大哭。
第二天,静音之钟被打开。内部设备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株巨大的蓝花苗。
我们没有庆祝胜利。
因为我们从未将他们视为敌人。
我们只是相信,没有人真的愿意永远沉默。
春天来了。
城市各处开出新的共感站点。学校开设“情感共振课”,教孩子如何识别并表达内心波动;医院设立“记忆疗愈室”,帮助创伤患者通过共鸣重建自我叙事;甚至连法庭也开始采用“共感证词”??当事人可在安全环境下分享真实感受,由系统验证情绪一致性,作为量刑参考。
最令人意外的是,联合国宣布成立首个“共感理事会”,由中国、挪威、哥斯达黎加三国联合提议,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的非暴力沟通机制建设。首任主席是一位盲人诗人,她说:“我看不见世界,但我终于听懂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