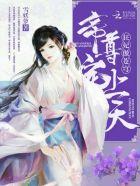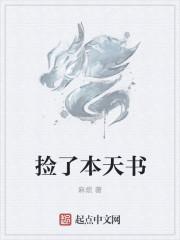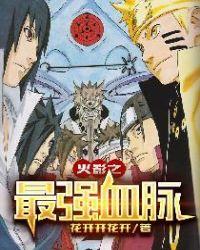笔趣阁>三国:昭烈谋主,三兴炎汉 > 第453章 新帝登基追谥刘备 汉中祖昭武皇帝(第2页)
第453章 新帝登基追谥刘备 汉中祖昭武皇帝(第2页)
几乎同时,幽州传来急报:马岱部遭遇不明敌军袭击,对方装备精良,战术诡谲,竟熟知羌胡作战习惯。鏖战三昼夜后,虽击退来敌,但损失惨重,粮道再度被截。最关键的是,敌军撤退前留下一面黑色旗帜,上绣银线古篆:“守旧继统,诛逆清君侧。”
李承业看完战报,久久不语。他召来木荣,沉声问道:“玄鹰卫最近可查到什么异常?”
木荣低头禀报:“我们在京畿周边发现了六处秘密联络点,均以药材铺或驿站为掩护。其中一处地下挖有密室,藏有大量‘牵丝散’成品及配药方。最惊人的是……我们在其中一间密室内找到了一台铜制机关,形似编钟,但能发出极低频之声波,与沈知微所述‘唤醒号角’频率一致。”
“果然是他们。”李承业闭目,“他们在用音律控制被下药的人。说不定……沈知微现在仍是清醒的,只是无法动弹。”
他猛地睁开眼:“立刻派人前往阴馆城,务必确保沈知微安全。另外,通知各地医馆,凡是收治‘无病因昏迷’患者者,立即上报,并严禁任何人探视,违者格杀勿论!”
与此同时,阿禾提出一个大胆设想:既然“牵丝散”需特定音律唤醒,那是否可用相反频率干扰其作用?她翻遍古籍,在一本失传已久的《南荒蛊经》中找到线索:“双生共鸣,逆律可破。”意思是,若能找到原声波的反相波段,便可解除控制。
黎?立刻组织工匠赶制一台“逆音器”,以编钟为基础,调校特定频率。试验初期屡屡失败,甚至导致一名志愿者短暂失聪。但在第七次尝试中,仪器终于奏效??一名被“牵丝散”控制三年之久的老学者突然睁眼,泪流满面,嘶哑喊出第一句话:“他们在……修改史书……每天……都有人在消失……”
这个消息让李承业震惊不已。他意识到,“影殿”不仅是一个政治阴谋集团,更是一场系统性的历史清洗工程。他们通过药物控制知情者,篡改档案,焚毁证据,甚至操纵舆论,只为维持那个虚假的“正统”叙事。
于是,他做出一项前所未有的决定:启动“薪火计划”。
所谓“薪火”,即是将新政理念与真实历史,以最原始的方式传递下去。不再依赖官方文书,不再仰仗朝廷权威,而是发动千千万万普通人,口耳相传,笔笔抄录,代代守护。
他在全国设立“传灯所”,招募识字百姓担任“薪火使”,每人负责一段《新政纪要》或《正统实录》的背诵与传播。这些文本被拆分成短章,加密成俚语歌谣,甚至编入童蒙读物。例如,《田律》第十章变成儿歌:“一亩三分地,官来也不许;谁若强夺去,全村打板子。”而关于赵皇后的故事,则化作民间戏文,在乡间舞台广为流传。
更令人震撼的是,许多盲人、聋哑人也主动加入。他们用手语、盲文、鼓点节奏记录法律条文,形成独特的“无声法典”。有村庄甚至发明了“石鼓传律”??每颁布一条新法,就在村口敲响特定鼓点,村民依律行事,世代不变。
短短一月,“薪火”已燎原之势席卷南北。就连边境戍卒也在战壕中传唱《兵役法》:“三年期满归故乡,不死不算阵亡!”每当夜深人静,篝火旁总有老兵低声讲述“那个被捂死的太子”和“那个不肯低头的宰相”。
而在这股洪流之中,一道新的威胁悄然浮现。
十二月末,一名年轻女子出现在长安街头。她衣着朴素,却举止优雅,自称是从交州来的游学士子。她在西市听了整整三天的“策园讲席”,然后提笔写下一篇万言策论,题为《法出于民,岂容独断?》,公开质疑李承业“借民之名,行专政之实”,认为真正的法治不应由一人主导,而应由全民共议。
文章一经张贴,立刻引发激烈争论。支持者称其“直指核心”,反对者则斥之为“巧言惑众”。但李承业看到此文后,却久久凝视,最后轻叹一声:“这个人……不简单。”
经查,该女子名为裴清漪,竟是裴元启的侄女,自幼送往南疆修行,精通音律、毒理、纵横之术。她并未加入“影殿”,却始终游走于黑白之间,似敌似友。
李承业下令请她入策园一叙。
当夜,两人对坐饮茶,窗外雪花纷飞。
“你为何归来?”李承业问。
“因为我想知道,”裴清漪淡淡道,“一个人究竟要多坚定,才能对抗整个时代的谎言。”
“那你找到了吗?”
她望着炉火,良久才说:“我看到了百姓脸上的光。那是我家族从未给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不会帮你,也不会害你。我只是想看看,这场火,到底能烧多久。”
李承业笑了:“那就看着吧。只要还有人愿意写字,愿意说话,愿意抗争,它就不会灭。”
裴清漪离去时,留下一枚小小的青铜铃铛,放在案上。铃内刻着一行细字:“声虽止,音未绝。”
李承业握紧铃铛,心中明白:斗争远未结束。
但这一次,他不再孤单。
寒冬最深处,春意已在泥土中萌动。
那些被压抑的声音,终将破土而出。
就像那块无字碑,虽尚未铭文,
却已承载万千人心的重量。
它等待的,不是一个名字,
而是一个时代共同写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