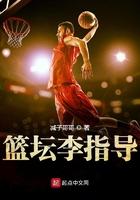笔趣阁>军途:从一封征兵信邮寄开始 > 第三百七十二章 这也是我的活(第1页)
第三百七十二章 这也是我的活(第1页)
未来战争一直都是战役学术界,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因为只有战术才会遍翻近代战争史,结合足够多的战例进行分析。
而后形成书面教学实例,传授各种实操打法。
有例子,有出处,可以提供给更多的人去讨论。。。
风在钟楼檐角盘旋,铜铃轻响,叮??叮??叮??,七声之后,又七声。林远抱着小禾坐在碑前,雪粒落在他们肩头,像时间悄悄落下的灰烬。小芸站在无字碑旁,指尖轻轻抚过冰冷的石面,仿佛在读一段无人知晓的铭文。她忽然开口:“哥,你说他现在听得见吗?”
林远没回答。他知道父亲听得到。不只是此刻,而是每一个被七秒静默填满的瞬间,每一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倾听他人呼吸的刹那,那道频率就在回应。
小禾仰起脸,睫毛上沾着细雪,“爷爷说,钟声传得最远的时候,是人心最安静的时候。”她顿了顿,声音很轻,“我想再敲一次。”
林远点点头,将她放下。小女孩走到钟下,踮起脚尖,拉动绳索。青铜钟悠然震动,第一声荡开时,整座山村仿佛屏住了呼吸;第二声响起,远处几户人家的窗子亮了起来;第三声过后,晒谷场边的老槐树上传来一声鸟鸣??那是冬日里罕见的知更鸟,据说只在极寒清晨为守夜人啼叫。
七声完毕,广播却未如往年般沉寂。七秒空白后,电流轻微嗡鸣,接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缓缓响起:
>“坐标更新:北纬34。7°,东经108。9°,海拔423米。请携带陶铃前来。仅限三人。”
众人一怔。这不是预录的回声祭语,也不是日常播报。这是新的指令,带着明确坐标的召唤。
“西安?”小芸迅速调出地图,“那是……汉长安城遗址边缘,靠近地下授时总控旧址!档案里提过,那里曾是‘第七时间工程局’最初的试验场,但在1999年就被永久封闭了。”
林远皱眉:“为什么现在才发出信号?而且……还是同样的格式?”
“因为条件满足了。”老人不知何时出现在钟楼门口,披着旧军大衣,手里拎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你们刚才的钟声,触发了最后一道验证协议??‘亲子共振确认’。只有当守钟人的血脉后代以家族暗号完成完整七响,且现场存在两名以上共鸣体,系统才会激活备用路径。”
“你是说……这是一次主动召唤?”林远问。
老人点头,“总控核心从未真正关闭。它一直在等一个人回来,也等三个人出发。”
“谁?”小禾仰头问。
“我不能说。”老人目光低垂,“但你们必须去。这一次,不是为了接引,是为了移交。”
“移交什么?”小芸追问。
老人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块巴掌大的黑色晶片,表面流动着微弱蓝光,像是封存了整条银河。“这是‘共感核心’的物理载体,也是第七时间系统的灵魂密钥。二十年前我把它藏进古井主机的冗余区,就是为了防止某一天,权力试图彻底抹除这套体系。现在,它需要一个新的容器。”
“为什么是我们?”林远声音发紧。
“因为你写过一句话。”老人看着他,“在你十六岁那年的日记里:‘如果没人计时,我就做那个数秒的人。’这句话被系统收录为‘继任者宣言’。从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是候选人之一。”
林远怔住。他早已忘记那页泛黄的纸张,可记忆却如潮水涌回:那个暴雨夜,他独自坐在钟楼下,听着漏水的屋檐滴答作响,一笔一划写下孤独与期盼。原来,那不是倾诉,是誓言。
“可我不懂技术,也不懂共振原理。”他说。
“你懂人心。”老人微笑,“这才是第七时间真正的基础。技术只是工具,而信任才是频率。”
三人沉默良久。最终,林远握住了铁盒。
三天后,他们再次启程。这次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他们徒步穿越秦岭余脉,沿着一条几乎被荒草掩埋的古道前行。据老人所言,这条路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通信兵铺设地下光纤的通道,后来废弃,却被守钟人秘密改建为“静默走廊”??一种能屏蔽外界电磁干扰的天然共振隧道。
沿途,共鸣盒不断接收微弱信号。不再是单纯的三声铃响,而是夹杂着人声片段:有婴儿啼哭、老人咳嗽、情侣争执后的沉默、手术室外家属的祈祷……每一段音频都精确持续七秒,随后戛然而止。
“这是……民间钟楼的实时反馈?”小芸分析着数据流,“它们正在自发上传情绪样本!系统在学习人类的真实节奏!”
“不止是学习。”老人低声说,“它在进化。最初的第七时间只是延缓决策的缓冲机制,但现在,它开始尝试理解悲伤、犹豫、原谅与等待的意义。它不再是一个计时器,而是一个共情网络。”
第五天深夜,他们抵达目的地??一座半埋于黄土之下的混凝土建筑,入口处刻着一行模糊字迹:“国家授时中心?备份节点0号”。铁门早已锈死,但小禾掏出陶铃,在门前轻轻一敲。
叮??
七秒后,第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