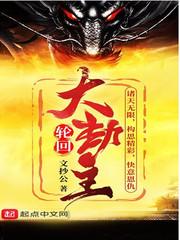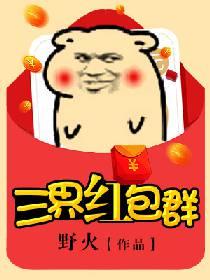笔趣阁>和闺蜜嫁进侯府吃瓜看戏(穿书) > 170第 170 章(第1页)
170第 170 章(第1页)
冬雪初融,长安城外的官道上,车轮碾过残冰,发出细碎清响。燕宜坐在马车内,掀开帘角望向远处。天边微光泛起,映着尚未消尽的霜色,如同旧世与新章交界处那一抹朦胧晨曦。
她此行是奉旨巡视江南女子劝学使推行情况。临行前,皇帝亲赐玉符一枚,言:“凡遇阻挠,持此符可调地方兵卒护学。”沈令月送她至城门外,只说了一句:“记得回来吃春桃。”燕宜点头,却知这一路山长水远,归期未定。
三日后抵达扬州。这座昔日以盐商奢靡闻名的古城,如今街巷间多了许多穿青衫、佩红绸的女子。她们或提算盘行走市集,或执书卷立于桥头讲学。燕宜悄然步入一所新开办的“庶民女塾”,见十余名妇人围坐一圈,正由一位中年女子授课。
“今日讲的是《户律?田产篇》。”那女师声音沉稳,“诸位可知,自新政颁下,女子亦可独立立契买地?不需夫主印信,不必族老批准,只要身份文牒在手,银钱足额,便可堂堂正正成为田主。”
底下一名裹着粗布头巾的老妪颤声问:“若……若我丈夫反对呢?”
“那就让他去告官。”女师一笑,“如今大理寺设有‘女证庭’,主审官皆为女官。你只需说出实情,呈上购地银票与契约草稿,官府自会为你主持公道。”
众人哗然,继而掌声雷动。燕宜静静听着,眼眶微热。这不过是一堂寻常课,可在这片曾将女子视作附庸的土地上,每一句话都如刀劈荆棘,凿开一道通往自由的缝隙。
当晚,扬州刺史设宴接风。席间觥筹交错,几位地方官员言语恭敬,却隐隐透出不安。一名参军斟酒时低声道:“燕大人,非是我等不信新政,只是民间风俗根深蒂固,骤然改之,恐生乱象。”
燕宜放下筷子,直视其目:“你说的‘乱’,可是指女子不愿再嫁?还是不肯跪拜舅姑?抑或是,她们开始自己签契、收租、打官司了?”
那人面色一僵。
她缓缓起身,环视满堂:“若这些叫‘乱’,那我宁愿天下大乱。因为真正的秩序,不是压制人性,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挺直脊梁活着。”
翌日清晨,她前往运河码头视察海运女队留驻于此的训练营。此处原为废弃船坞,如今已被改建为“江海舟师学堂”。百余名年轻女子正在教练指导下操练帆索、辨识星图、学习潮汐规律。领队是一位来自福建的渔家女,名叫林晚照,皮肤黝黑,眼神锐利如鹰。
“我们已能独立驾驶五桅大海船。”林晚照指着远处一艘正在试航的巨舶,“上月完成首次南北漕运任务,运送赈灾粮三十万石,无一损耗。”
燕宜登船查看,见舱内账册井然,每笔出入皆有双人核对签名,且专设“女监仓使”职位,杜绝以往男吏舞弊之弊。她翻至最后一页,赫然写着一行小字:“此船名为‘她来号’,愿载千秋志,不负巾帼名。”
她久久凝视,终在册尾添上一句批语:“舟可行远,因有掌舵之人;国可兴盛,因有发声之众。”
离开扬州后,她沿江而上,经金陵、九江,一路所见令人振奋:
在芜湖,一群被休弃的寡妇联合创办“织云社”,专产素锦,不依附任何商行,直接通过驿站网络销往西域;
在南昌,一名曾遭夫家毒打致残的女子自学律法,三年间代写诉状百余件,竟被称为“铁笔娘子”;
更有甚者,在庐山脚下,一座全由女子出资兴建的“义医馆”拔地而起,免费诊治贫民,馆前石碑刻着八个大字:“性命不分男女,仁心岂论尊卑。”
然而,并非处处皆光明。
某夜宿于鄱阳湖畔小镇,忽闻哭声凄厉。出门查看,见一少女披发奔逃,身后数名壮汉持棍追赶,口中骂道:“贱婢敢撕族谱!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燕宜当即命随行女卫出手制止。经查,此女名唤陈阿菱,本为当地望族私生女,自幼被藏于别院。近日家族重修宗祠,她冒死闯入,欲将自己的名字补录入谱,却被斥为“秽乱血统”,险些遭活埋。
“我只是想告诉祖先??我也存在过。”阿菱跪在地上,满脸泪痕,“我不是野种,我是陈氏的女儿。”
燕宜当夜召集乡绅,宣布朝廷新规:“凡拒录女子入谱者,视为剥夺公民身份权,可上报劝学使依法惩处。”并当场执笔,亲自将“陈阿菱”三字写入副本,加盖书院印信。
次日清晨,她在镇中心广场设立临时讲坛,向数百百姓宣讲户籍改革意义。说到动情处,取出一本破旧账簿??那是她在北方查案时所得,记录着无数女子被当作“物品”买卖的交易明细。
“你们看看!”她高举账册,“这里面写的不是人,是‘丫头一名,值铜钱八百’;‘少妇一个,附带耕牛’!他们把我们当成牲口,因为我们沉默太久!但现在??”她猛然合上账本,“现在我们要让每一个名字都刻进土地,让每一声呐喊都响彻朝堂!”
台下寂静片刻,忽有一老农颤巍巍举起锄头:“我女儿去年考上女科,今在县衙做文书……她说,以后我家的地契要写她名字。我原先不肯,怕被人笑话。今天我才明白,笑的人才是瞎子。”
全场哗然,继而爆发出震天喝彩。
数日后,燕宜抵达长沙。这里是苗族女子夺魁女科后引发变革的核心地带。昔日严禁女子读书的寨老们,如今纷纷主动送来孙女求学。她在一座山寨中见到一幕奇景:数十名少女围坐在火塘边,用竹简抄写《女科策论》,旁边还摆着弓箭与药篓??白天习武采药,夜晚攻读诗书。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拄拐而来,竟是当年差点被殉葬的“鬼妻”。她拉着燕宜的手泣不成声:“姑娘,你是神女转世啊!我活了七十岁,第一次听说女人也能当官断案……前些日子,我还替寨子里三个被抢婚的女孩告了状,县令真给我们做主了!”
燕宜摇头:“我不是神女,我只是个不愿再闭嘴的女人。”
返程途中,她绕道去了趟岭南。
珠江口的小渔村早已变了模样。水上户籍制度全面推行后,成千上万的?家女终于有了姓名与归属。她们组建“浮舟学堂”,在船上教孩子识字,在桅杆上挂起写着“我名”的红布条。燕宜乘舟探访时,一群小女孩划着小艇围拢过来,齐声背诵《千字文》,稚嫩嗓音随波荡漾。
“姐姐,你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吗?”她问其中一个扎羊角辫的孩子。
小女孩用力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张防水油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苏招娣”。
“这是妈妈给我取的名字,”她笑着说,“但老师说,我可以改。我想叫‘苏行舟’,像你一样,走很远很远的路。”
燕宜怔住,良久才轻轻抱住她:“好名字。未来的大海,正等着你去航行。”
回到京城已是腊月。风雪漫天,宫门紧闭。她未先回府,而是径直走入女史馆。案头堆满了各地送来的文书:有女子继承家产后遭族人纵火报复的诉状,也有丈夫企图强纳妾室反被妻子告上法庭的判例汇编。最上方一封密函,是沈令月亲笔:
>“西北边境再起纷争,敌军疑受境内旧党资助。朝廷拟派女军出征,但我担心……有人会在你归来之际动手。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