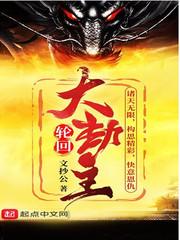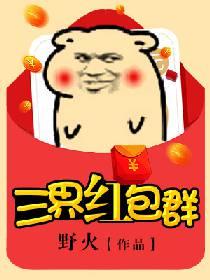笔趣阁>和闺蜜嫁进侯府吃瓜看戏(穿书) > 170第 170 章(第2页)
170第 170 章(第2页)
她吹亮烛火,正欲研墨复信,忽觉窗棂轻响。回头望去,一只灰羽信鸽停在檐下,脚上绑着极细的竹管。取下展开,仅八字:“子时三刻,东厢有变。”
她不动声色,召来心腹女卫部署埋伏,自己则佯装疲惫就寝。至子时,果见数条黑影潜入东院,目标直指存放《她声集》手稿的铁柜。双方交手不过片刻,刺客悉数落网,为首者竟是前礼部侍郎的幼子,身上搜出一份名单??上面列着三十多名活跃女学者的名字,每人旁标注“可胁”、“可污”、“可除”三类标记。
天明后,案件移交大理寺女庭审理。燕宜亲自出庭作证,当众宣读那份黑名单,并展示近年来保守势力如何系统性打压女性觉醒:散布谣言、贿赂媒婆阻婚、煽动家族逼嫁、甚至雇佣江湖术士制造“女子读书必遭天谴”的谶语。
庭审持续七日,全程向民间开放。每日都有成百上千女子前来旁听。第七日结案陈词时,主审女官霍青娥站起身,面向公众朗声道:
“今日我们审判的不只是几个刺客,更是延续千年的偏见与暴力。法律若不能保护弱者开口的权利,那它就不配称为法律。从今往后,任何试图以恐惧迫使女性沉默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国家根基的背叛!”
判决下达:主犯斩监候,其余流放极南荒岛,终生不得返陆。同时,皇帝下诏增设“言论庇护令”,凡因倡导性别平等而遭受威胁者,可申请朝廷保护,安置于安全居所。
风波平息后,燕宜再度登上雁门关。
这一次,她带来了一面旗帜??纯白底色,中央绣着一朵盛开的莲花,周围环绕三百一十七个名字。那是自书院创立以来,所有为女性权利献身者的名录,包括那些死于抗婚、殉学、战阵、狱中的无名者。
“该让她们被看见了。”她对沈令月说。
两人合力将旗升上城楼最高处。寒风吹拂,莲纹猎猎作响,仿佛无数灵魂在低语。
不久之后,首届“女子议政大会”正式召开。百名代表齐聚太极殿侧厅,涵盖农妇、商贾、医者、将士、工匠、乐师各阶层。议题涉及教育普及、婚姻法修订、劳动保障、边防策略等十余项国政。
苗族代表提出“山地女子垦荒免税”提案,获多数支持;
海运队长建议设立“海上女驿”,方便远洋女船员补给休整;
更有人大胆提议:“应允许女子参军授勋,组建常备女军部队。”
争论激烈,气氛炽热。有男臣讥讽:“妇人干政,岂非乱纲?”
随即一名年轻女代表起身反驳:“请问大人,您可曾见过戍边女兵破敌冲锋?可曾听过灾区妇孺自救互救?若这叫‘乱纲’,那我宁愿纲纪崩塌,也要换一个公正人间!”
满座默然。
最终,十七项提案通过审议,送呈御览。皇帝阅毕,朱笔亲批:“准行。此乃新时代之始,不可缓也。”
散会那日,燕宜独自走到皇宫后苑的桃林。当初移植于此的那株小树,如今已亭亭如盖,花开满枝,粉霞般笼罩半空。她伸手轻抚树干,忽然发现树皮上被人悄悄刻下一排小字:
>“谢谢你,让我活成了想要的样子。”
她笑了,眼角沁出泪光。
当晚,她提笔续写《她声集》终章:
>“这条路没有尽头,因为它本身就是答案。
>我们不是要推翻什么,而是要重建一种可能??
>在那里,女孩出生时不被叹息;
>女人说话时不被嘲笑;
>母亲老去时不被遗忘。
>
>历史不会自动进步,它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往前挪动一寸。
>而我有幸,见证了这寸进的光芒。
>
>若有一天,人们不再惊讶于女子为官、掌兵、治学、立法,
>那便是真正的太平盛世。
>
>到那时,请记得,曾有一群女人,
>不肯低头,不愿沉默,不甘死去。
>她们来了,
>并且,永远留下了足迹。”
合上书页,窗外春风拂过,桃花簌簌飘落,如雨,如誓,如永不熄灭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