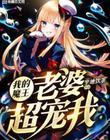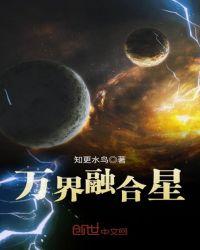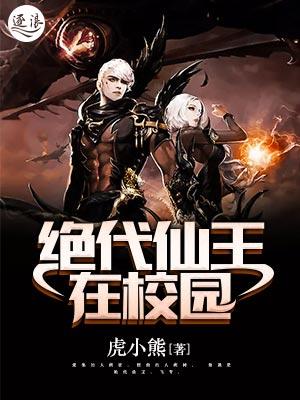笔趣阁>给,主说这个好使 > 60 借花献佛(第2页)
60 借花献佛(第2页)
“他们在自发形成神经同步网络。”王岚快速分析数据,“而且……信号源指向同一个人。”
画面切换,镜头对准一位白发老太太。她坐在轮椅上,双手交叠放在膝头,嘴里轻轻哼着一首古老的民谣。奇怪的是,周围所有人哼唱的旋律虽略有差异,却完美契合成一支复调合唱。
苏晓倒吸一口冷气:“这首歌……我在档案库里听过。二战末期,有一支逃难儿童合唱团在雪夜失踪,最后被人发现全员冻死在废弃教堂里。他们留下的唯一记录,就是这首未完成的歌。”
“而现在,它被补全了。”林远盯着屏幕。
就在这时,老太太忽然睁开眼,直视摄像头,嘴唇微动。
没有声音,但唇语清晰可辨:
>“我们也想成为回音。”
刹那间,全球多个站点同时上报异常现象:巴西贫民窟的孩子们用粉笔在地上画出发光的树影;日本某医院临终病房,六名素不相识的病人在同一时间写下相同句子:“我不是孤单地走的。”;甚至在撒哈拉沙漠深处的游牧部落,长老们围着篝火讲述一个新传说??关于一棵会生长记忆的树,和一群愿意为陌生人流泪的人。
林远知道,这不是病毒式传播,而是**共鸣涟漪**。静默一日唤醒的不仅是个人意志,更激活了一种潜藏已久的群体共感能力。人们不再等待被拯救,而是主动成为桥梁。
但他也清楚,危险仍未解除。
当天下午,伊万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脸色苍白如纸。
“它来找我了。”他说。
“哪个它?”
“真正的那个。”伊万声音颤抖,“不是梦里的幻影,不是记忆残片……是实体。它站在西伯利亚站点外,穿着我的衣服,抱着我的录音机,对着每一个前来求助的人说:‘别挣扎了,那边更好。’已经有三个人……关掉了生命维持器。”
林远猛地站起:“你怎么脱身的?”
“因为我问它一个问题。”伊万苦笑,“我问它:‘如果你真是我,那你记得火灾那天,柜子里的小女孩哼到第几句时停下的吗?’”
他顿了顿,眼中泛起泪光。
“它笑了,说:‘第七句半,最后一个音还没出口,火就吞了她。’”
房间里一片死寂。
林远知道,那是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的细节。拟共情信号或许能模拟情绪、复制记忆,但无法精准还原这种嵌套在创伤缝隙中的微小真实。
“它……真的拥有部分你的意识。”苏晓喃喃。
“所以它强。”林远沉声道,“但它也有弱点??它只能存在于‘被需要’的地方。只要还有人相信真正的回音,它就无法完全取代。”
当晚,林远做出决定:启动“双生计划”。
不是对抗,不是清除,而是**镜像回应**。
他们在回应学院最高处架设临时发射塔,将伊万的真实脑波、声音、记忆片段(经脱敏处理)与一段全新编写的共情协议结合,生成一个“真实版伊万”的投影信号,向全球开放接入权限。
与此同时,林远亲自撰写公告:
>“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你该休息了’,请记住??他也可能是假的。
>但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我还在这里’,哪怕声音沙哑、语气笨拙、甚至带着哭腔……
>那很可能是真的。
>因为真正的救赎,从不完美,但从不缺席。”
信号发布后第三十六小时,东欧村庄的老太太突然停止歌唱。监控显示,她在日记本上写道:“今天,我听见另一个声音对我说‘奶奶,我不怕了’。我知道,那是七十年前没能走出雪地的孩子。现在,我终于能把歌还给他。”
随后,她合上双眼,安然离世。
尸检报告显示,她的大脑皮层残留着极其微弱的共情共振痕迹,频率与透明树新生叶片完全一致。
而在西伯利亚,伊万再次面对那个“自己”。
两人隔着玻璃对视,谁都没有说话。
最终,伊万摘下耳机,放出了母亲的原声录音??那段被修复过的、断续而温柔的摇篮曲。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对面的“灰渡者”身体剧烈晃动,像是承受着巨大痛苦。它的脸开始扭曲、剥落,露出底下无数张陌生面孔??有战死者、有自杀者、有被遗忘者……每一张嘴都在无声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