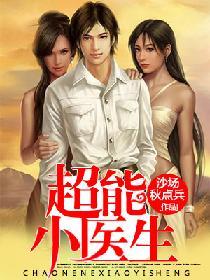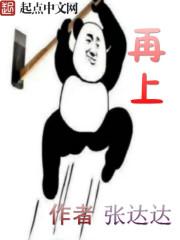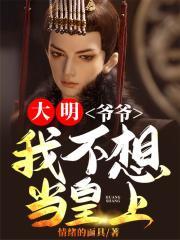笔趣阁>千禧:我真不想当大导演 > 第829章 翻天覆地的改变(第2页)
第829章 翻天覆地的改变(第2页)
车子驶出十里,王小军突然回头,看见山坡上有个小小身影正用力挥手。
林有攸闭上眼,没说话,只是把掌心贴在车窗上,仿佛能隔着风雪触碰到那一声未出口的“再见”。
回到城市一周后,《听?见》AR展览第二站落地成都。这次的主题是“家庭中的无声战场”。展厅中央设置了一个模拟客厅,观众戴上眼镜后,会看到一家三口吃饭的画面。起初一切正常,直到父亲一句“你怎么这么笨”响起,餐桌上的食物开始变灰,墙壁浮现裂痕,孩子的影子逐渐缩小、透明。
最震撼的是互动环节:系统会采集观众微表情和呼吸频率,当检测到逃避意图(如低头、后退),画面立即切换成一段真实录音??
“那天我爸摔了我的琴。他说练琴没用,迟早要送外卖。我躲在厕所哭,可我知道,就算说出来,也没人觉得这算伤害。”
展览开幕当天,一位母亲在体验结束后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后来写下留言:“我儿子上周自残了。我一直怪他心理脆弱。现在我才明白,是我亲手关掉了他的声音。”
类似的故事不断涌现。有人开始清理家中监控摄像头,有人撕掉了写满“必须优秀”的家庭公约,还有夫妻抱着彼此道歉:“这些年,我们都只顾着纠正对方,忘了问问为什么痛。”
与此同时,“反向共鸣计划”迎来首个成功案例。一名曾在网上发布“抑郁症都是矫情”的博主,在参加沉浸式倾听后公开道歉,并捐出账号收益设立“倾听奖学金”。
他在视频中哽咽:“我以前以为坚强就是不说痛。现在才知道,真正的坚强,是痛着还能选择相信有人愿意听。”
然而风暴从未真正停歇。
某晚,林有攸刚结束一场线上培训,张慧敏紧急来电:“系统监测到境外IP批量抓取匿名投稿数据,手法与公安部通报的犯罪团伙高度一致。更糟的是,他们已经开始剪辑拼接,准备推出所谓‘中国青少年精神崩溃实录’纪录片,在海外平台预售。”
“来源锁定没有?”
“初步追踪到东南亚服务器中转,幕后操作者使用深度伪造身份。但我们发现一个漏洞??他们在下载时未完全屏蔽行为轨迹,留下了音频解码偏好的特征。这种偏好,只出现在特定情报训练体系中。”
林有攸眼神一凛:“军方背景?”
“极有可能。而且……”她顿了顿,“他们窃取的内容里,包含了‘拾声者’纪录片的部分未公开素材,包括王小军在救助站拍摄的一个流浪少年讲述被亲生父亲虐待的经历。”
林有攸猛地站起:“通知小军,立刻备份所有原始母带,物理隔离存储。同时启动‘回声盾’协议,对全平台数据进行动态混淆加密。另外,把那份犯罪档案重新整理,标注技术细节,直接递交给国安部门。”
两天后,国家网信办发布公告,依法查处一批传播恶意扭曲信息的境外媒体账号,冻结相关资金链。公安部披露,已抓获两名境内接应人员,均为某高校留学生,受境外组织蛊惑提供内部测试账号权限。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严肃指出:“心理健康公益项目不是意识形态攻击的突破口。任何企图利用民众苦难制造对立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风波渐息,但林有攸知道,这场较量的本质从未改变??有人想让痛苦保持沉默,而他们,誓要让它被听见。
春天来临前,“回声计划”迎来第10万次成功匹配。系统自动点亮了一颗虚拟星辰,命名为“第一万个回音”。那是一位聋哑少女的留言,通过手语翻译录入:
“我一直以为,听不见的人最孤独。后来才发现,说不出的话,才最重。现在我学会了写字,也学会了喊‘救命’。虽然声音别人听不到,但我的心,终于被看见了。”
这句话被刻进“倾听广场”新增的玻璃幕墙,阳光穿过时,字迹如金线流动。
清明节那天,林有攸独自前往郊区墓园。他在一座朴素的石碑前放下一束白菊,碑上刻着:“爱女陈心怡之墓,父陈志远立。”
他知道,真正的陈志远仍流亡在外,生死未卜。但他坚持每年来此祭奠,既是对那个跳井女孩的告慰,也是对自己初心的提醒。
离开时,他在墓园门口遇见一位老人,正颤巍巍地往信箱里投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给所有不敢哭的孩子”。
老人说:“我孙子去年自杀了。遗书里只有一句话:‘你们总要我开心,可我连不开心都不敢说。’我现在每天写一封信,寄给‘回声计划’,希望至少能替他说完那些没说的话。”
林有攸接过信,郑重放入背包:“我们会替您念给他听的。也会让更多孩子知道,不开心,也可以。”
回到工作室,他召集全体成员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
“我们不能再被动防御。”他说,“从今天起,启动‘种子教师计划’。在全国遴选一千名基层教师、社工、医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倾听技能培训。目标不是让他们成为心理咨询师,而是成为‘第一个愿意蹲下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