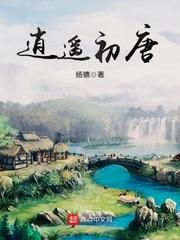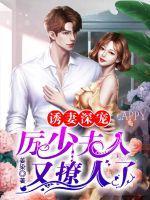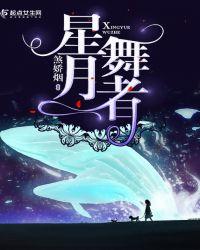笔趣阁>千禧:我真不想当大导演 > 第829章 翻天覆地的改变(第1页)
第829章 翻天覆地的改变(第1页)
第N次因为林无攸而发生网络崩溃时,微博的诸位秃头程序员摸摸光秃秃的头顶,强行露出心如止水的笑容。
不气,不气,气坏身体无人替。
不气,不气,不??
啊啊啊!!
程序员还是没能忍。。。
雪落得越来越密,林有攸站在阳台上,任寒风吹动衣角。磁带里的声音循环了三遍,他才缓缓按下停止键。那句“我想活下去”像一根细线,轻轻缠住心脏,拉得生疼又温暖。
他回到屋内,把随身听小心地放进抽屉最底层,上面压着一本泛黄的《电影美学导论》??那是他大学时代唯一的信仰。如今书页间夹着的不再是剧本草稿,而是一张张从“回声计划”中打印出来的用户留言条:“谢谢你没有关掉我的录音。”“我今天第一次对老师说‘我不舒服’。”“原来我不是累,是难过。”
手机再次震动,是张慧敏发来的系统警报:**编号HN-107429用户连续七日触发高危情绪模型,语音频谱显示极端压抑倾向,最后一次提交录音为呼吸声持续18分钟,无语言内容。**
林有攸立刻拨通王小军电话:“小军,去查这个ID对应的地理热力图,优先匹配最近的心理援助志愿者。”
“已经在处理。”王小军声音沙哑,“但……这孩子住在甘肃陇南一个几乎没信号的山村,上次我们派心理老师进村,走了六小时山路。现在大雪封路,车根本上不去。”
“那就徒步。”林有攸斩钉截铁,“联系当地教育局,协调一名熟悉情况的村干部带路。费用、装备、应急药品,全部由LINStudios承担。再调两个会手语的志愿者,万一孩子已经拒绝说话,我们也得能沟通。”
挂了电话,他打开“声音漂流箱”的后台地图。密密麻麻的光点遍布全国,每一个都代表着一段被倾听过的独白。可在这片广袤之中,仍有大片灰色区域??那里的人从未注册,也未曾触碰过那个小小的录音按钮。
他忽然想起郑文轩老人临走前说的话:“重建耳朵,比制造喇叭更难。”
第二天清晨,林有攸亲自带队出发。飞机转大巴,再换皮卡,最后步行。积雪没过脚踝,山风割面如刀。同行的心理专家李婉三十岁出头,曾在汶川地震后驻扎灾区三年,她说:“很多孩子不是不想说,是他们试过太多次‘没人听’。”
第三天中午,他们抵达目的地??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学。教室窗户糊着旧报纸,操场上结着薄冰。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周,见到他们时眼圈瞬间红了。
“HN-107429是我们班的小岩。”她低声说,“爸妈在外打工五年,奶奶去年去世。他从去年开始就不怎么说话,作业本上全是涂黑的格子。我们让他画画,他画了一整本黑色太阳。”
“他现在在哪?”
“在教室,一个人。”
他们轻轻推开教室门。男孩蜷在角落课桌下,怀里抱着一台老旧MP3,耳机紧紧贴在耳边。听见动静,他猛地抬头,眼神像受惊的小兽。
林有攸蹲下来,不靠近,也不说话,只是从包里拿出一台迷你录音笔,放在门口的讲台上。然后他按下录制键,轻声说:“我是林有攸。我也曾经很久不敢说话。但我发现,只要有一个声音愿意留下来,世界就不会彻底黑下去。”
说完,他退到门外,留下空间。
一个小时后,小岩爬出来,颤抖着走到录音笔前。他盯着它看了很久,终于开口,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我……梦见奶奶回来了。她说想听我背古诗。我背了,她笑了。可醒来发现,我已经忘了她的脸长什么样。”
他说完就跑开了。
但这已足够。
当晚,林有攸团队在校舍临时架设设备,启动“移动倾听站”。孩子们排着队来录下心里话。有的说“我想爸爸回来”,有的说“我偷吃了同桌的饼干对不起”,还有一个小女孩认真地说:“我希望春天早点来,这样花开了,妈妈就能拍照发朋友圈夸我好看。”
这些声音被加密上传,同步生成AI诗歌,通过邮件发送给远在他乡的父母。
三天后离开时,小岩站在校门口,远远地看着他们。临行前,林有攸让王小军把一台新录音笔留在讲台,里面预录了一段话:
“小岩,你不是沉默,你在等一个安全的声音。现在,轮到我说了:我在听。下次见面,我想听听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