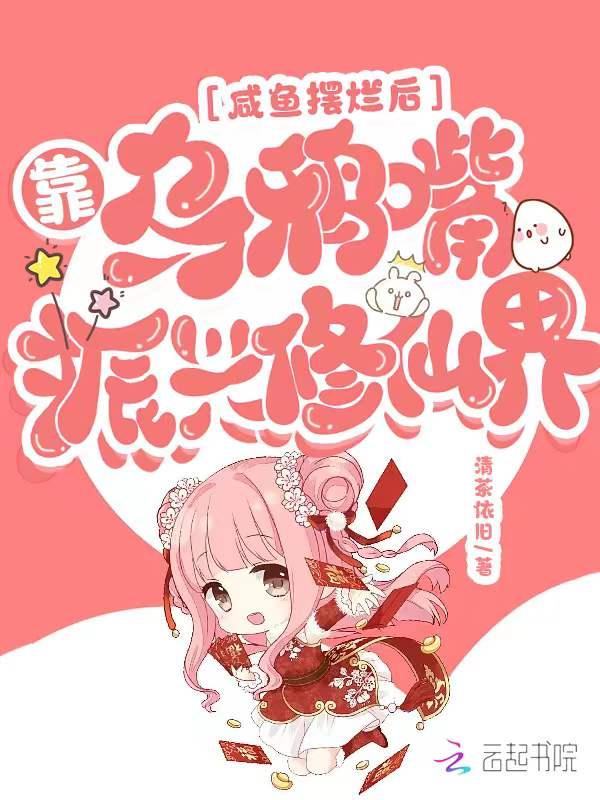笔趣阁>旧时烟雨 > 第六百零七章(第1页)
第六百零七章(第1页)
在媳妇似笑非笑的注视下,陈宣脑袋里面瞬间浮现出了缥缈仙子听音的身影。
初见时的朦胧神秘,解开面纱后婴儿般嫩白的肌肤,环佩叮当赤足露小腿萝莉一样的活泼装扮,倾国倾城的少女容颜,完美比例凹凸有致的火。。。
风起时,海面如墨色绸缎般翻卷,浪头拍打着冰封的岸线,发出沉闷的回响。那本《东海百家录》在陈砚手中微微发烫,仿佛有生命般搏动着。纸页泛黄,边缘被海水泡得微卷,却奇异地未损一字一句。他一页页翻过,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旁注生辰、卒年、事迹,甚至还有几句家训、一首童谣、一段渔歌??那是早已失传的“潮音调”,据说只有东海深处的渔民才会哼唱。
“林昭,生于永和三年冬月十七,卒于永和三十七年六月初九。妻亡于瘟疫,子幼溺海。曾任县学教谕,因上书言税赋不公,贬谪边陲。后聚民抗暴,举义于白沙港,兵败身死,族人尽诛。遗言:‘灯若不灭,我终归来。’”
陈砚念到这里,指尖一颤。这八个字,竟与第九笛初醒之时在他梦中低语的内容一模一样。他猛地抬头望向老渔夫,声音沙哑:“您……梦见的那个蓝衫女孩,长什么样?”
老人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恍惚,喃喃道:“约莫七八岁年纪,左耳垂有一颗小痣,手里攥着半截红绳……她说她叫‘阿昭’,是林家最后的血脉。”
陈砚心头剧震。阿昭??昭者,光也。不是名字,是期盼。是林昭临死前未能托付的孩子,在冥冥之中借梦境传递火种。
他忽然明白,无名碑之所以能在千年之后苏醒,不只是因为第九灯将亮,更是因为有人从未真正忘记。那些被斩草除根的家族,并未彻底断绝;他们的记忆藏在海底的册子里,埋在祖母口中的歌谣里,刻在孩童无意识涂画的灯塔上。只要还有一个名字被人记住,就还有一线归途。
远处天际,灰雾仍未散尽,反而在东南方凝成一座巨大的漩涡,如同天空裂开了一只眼。柳念安的罗盘在净尘走后便不断震颤,此刻指针疯狂旋转,最终停在一个方向??**青崖山**。
那是朝廷设立的“正史阁”所在之地,号称收藏天下典籍,实则专司删改、焚毁“悖逆之书”。历代帝王皆以“定鼎正统”为由,命人将不利于当权者的记录尽数销毁,连带牵连者的名字也要从所有文献中抹去。而今,那里正燃起冲天黑烟,浓烈的焦味随风传来,夹杂着纸灰如雪,飘落在这片雪原之上。
“他们在烧。”陈砚低声说,心口的玉印骤然灼热,“这一次,不只是抹去名字,是要把根都烧成灰。”
他挣扎起身,双腿仍因方才吹奏第九笛而酸软无力,可脚步却异常坚定。他知道,若任由他们继续焚烧族谱,那些刚刚解脱的灵魂或将再度迷失,甚至连轮回之路都会被斩断。记忆一旦彻底湮灭,便是真正的死亡。
就在此时,海风送来一阵极轻的笛声。
不是双鱼玉笛,也不是第九笛,而是某种极为古老的骨笛,音色苍凉如泣,像是自地底深处传出。紧接着,渔船四周浮现出数十艘虚影船只,皆破败不堪,桅杆断裂,船身布满刀痕箭孔。每一艘船上,都站着模糊的人影,手持渔叉、扁担、锈剑,默默注视着陈砚。
老渔夫跪伏在地,额头触雪:“这是……三百年前白沙港起义的船魂。他们一直在等一个人,能把他们的名字带回陆地。”
陈砚深吸一口气,将《东海百家录》紧贴胸口,对着众魂深深一拜:“今日,我不只为你们发声,更为你们回家。”
话音落下,他再次举起双鱼玉笛,却不吹曲,而是以指叩笛,三短一长,正是当年渔民传递紧急信号的暗号??**“血书未冷,灯塔犹存”**。
刹那间,整片海域沸腾起来。
无数光点从海底升起,汇聚成河,缠绕着那些虚船,使之渐渐凝实。破损的帆重新张开,上面赫然绣着一个褪色的图腾:**一盏孤灯,立于礁石之上,光照四方**。那是白沙港渔民世代信奉的“守灯神”,实则是对正义与记忆的象征。
船队缓缓启航,破冰前行,直指青崖山方向。陈砚立于首船船头,衣袂猎猎,心口玉印与海波共鸣,隐隐传出心跳般的节奏。他知道,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救援,而是一场对“遗忘权”的反攻。历史不该由胜利者书写,更不该由权力者抹杀。每一个曾活过、爱过、抗争过的人,都有权利留下痕迹。
三日后,船队抵达青崖山外十里。
山势险峻,云雾缭绕,九重宫阙依崖而建,金瓦朱墙,气势恢宏。然而此刻,正史阁顶层烈焰熊熊,黑烟滚滚,数百名黑袍执事手持火把,在广场中央堆起高高的书山,一本本族谱、账册、民间志书正在化为灰烬。空中悬浮着一面巨大铜镜,镜面映照出无数扭曲文字,皆是被删除的名字,正被一道无形之力强行碾碎,化作飞灰。
“那是‘忘鉴’。”柳念安不知何时已返回,脸色苍白,“传说中由初代帝王以万人怨念铸成,能吞噬记忆,使人连‘曾经存在过’这件事都彻底否定。一旦它吸收足够多的姓名,便可重塑世人认知,让篡改的历史成为唯一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