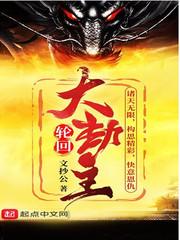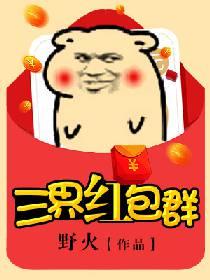笔趣阁>这顶流醉酒发癫,内娱都笑喷了! > 第168章被教训的全之龙IU来访(第1页)
第168章被教训的全之龙IU来访(第1页)
在杜胖子看来,全之龙作为国际友人来参加国内的比赛,吕铭不说像他一般毕恭毕敬,至少也得很有礼貌的跟全之龙打打招呼什么的,更别说人家全之龙主动来寻找吕铭这个糊咖了。
而吕铭这个糊咖不仅没有展现出一点。。。
陆钏没有立刻关闭录音软件。他盯着屏幕上那条刚刚生成的波形图,像在辨认某种密码。它起伏平缓,尾音微微上扬,仿佛一句话说完后还悬在空气里不肯落地。他知道,这句话此刻正穿过光纤、跃过基站、经由“心流网络”的无数节点流转??也许下一秒,就会出现在某个深夜未眠的人耳中。
窗外天光渐暗,槐花落在键盘上,被风扇轻轻吹动。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苏黎发来的消息:“‘种子回声’第十七批设备已运抵云南怒江,当地教师反馈说孩子们用广播给山对面的亲人唱歌,有人隔空回应了。”后面附了一段音频。
陆钏点开,风声很大,夹杂着断续的童声:
>“阿爸,今天我学会写名字啦!”
稍顿片刻,远处传来模糊却清晰可辨的回答:
>“囡囡??!”
声音粗粝,带着山地人特有的沙哑,却震得人心口发烫。接着是一阵笑,不知是谁先起头,两边的人都唱了起来,调子跑得离谱,歌词也听不清,但那种跨越峡谷的应和,像是大地自己发出的共鸣。
他闭上眼,想起父亲最后一次排练时说的话:“音乐不是用来展示完美的,是用来连接残缺的。”
那时他不懂,只觉得这话太软弱。如今才明白,所谓完美,不过是拒绝真实的一种借口。而真正的连接,从来都发生在裂缝之中。
工作室门被推开,秦澜走了进来,手里抱着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外壳斑驳,旋钮松动。“这是从内蒙古一个牧民家收来的。”她把机器放在桌上,“他们用‘种子回声’改装了这台六十年代的老家伙,接上了太阳能板。过去三个月,每天晚上八点准时播放《春江花月夜》,方圆十里都能听见。”
陆钏伸手摸了摸那冰凉的金属外壳,指尖触到一行刻痕极深的小字:“听见你了,额吉。”
“额吉”是蒙古语里的“母亲”。据说那位牧民老人年轻时因家庭变故与母亲失散,几十年杳无音信。直到某天夜里,他在帐篷里听到这段旋律,忽然听见广播里混着一句极轻的哼唱??那是他母亲小时候常给他唱的摇篮曲片段。
他不信邪,录下来反复听,终于在次声波频段捕捉到一段微弱的人声采样,虽无法确认来源,但他坚信那就是她。第二天一早,他就骑马翻山越岭,找到附近信号最强的那个转发站,在设备背面发现了同样四个字:“听见你了”。
“我们查过了,那段哼唱确实不属于原曲。”秦澜低声说,“但它被‘地鸣计划’无意中拾取,通过地质监测站传到了那里。可能是某个志愿者录入本地民谣素材时顺手加进去的……没人知道是谁。”
陆钏笑了。这世界最奇妙的事,往往不是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是无数微小善意在时间中偶然共振的产物。
“云镜那边呢?”他问。
“还在动。”秦澜神色凝重,“他们最近注册了一批新账号,伪装成乡村教师和社区工作者,申请接入‘种子回声’系统。初步筛查发现,其中有七套设备在上传经过篡改的心理诱导音频,内容伪装成‘冥想引导’,实则植入潜意识指令,试图制造群体焦虑。”
陆钏不意外。敌人越是无力正面击溃你,就越会钻进你的血管里腐化你。
“处理掉了吗?”
“已经隔离并反向追踪。”秦澜顿了顿,“但我们不能封得太狠。一旦切断所有可疑通道,普通人也会失去信任。现在的情况是??谁都说不清谁是真的。”
陆钏点头。这正是沈砚预言的局面:当真相与谎言共用同一套语言,最大的武器不再是传播,而是辨别。
他起身走到墙边,拉开抽屉,取出父亲留下的笔记本。翻开最后一页,上面有一行从未示人的笔记:
>“若有一天此曲为人所惧,请记住:
>它诞生于寂静,而非喧嚣;
>它属于倾听者,而非掌控者。”
他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忽然转身打开电脑,调出“人间低语”数据库底层协议。手指飞快敲击键盘,植入一段新的验证机制??基于生物反馈的身份认证系统。只有当接收端用户在聆听过程中产生特定情绪波动模式(如泪腺激活、心率同步、呼吸放缓),才会解锁完整音频内容。AI伪造的情感无法触发这些生理反应,因此再高明的合成语音也将失效。
“叫它‘心跳密钥’吧。”他对秦澜说,“真正被打动的人,自然能打开门。”
三天后,升级版系统上线。首批启用该功能的是西藏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那里有三十多名听障儿童正在学习骨传导音乐疗法。老师让他们把手贴在音箱表面,感受震动节奏。当《春江花月夜》响起时,仪器记录到孩子们的大脑α波显著增强,其中一名自闭症少年第一次主动拥抱了同伴。
当晚,一段视频悄然走红。画面中,一个小女孩戴着助听器,闭着眼睛用手跟着节拍画圈。突然,她睁开眼,指着天空喊:“妈妈!我听见月亮唱歌了!”
评论区瞬间泪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