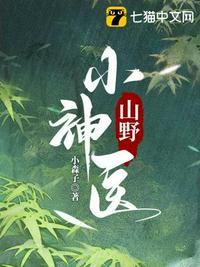笔趣阁>皖东人家 > 第二百七十二章 申诉(第1页)
第二百七十二章 申诉(第1页)
已是深夜了,树杰仍辗转难眠。母亲含辛茹苦带着他们一路走来的画面,如同无声的电影,一幕幕在眼前浮现。如今日子总算好了,她却含冤九泉,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如同一把钝刀,在他心口反复磨蹭,让他痛彻心扉。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迷迷糊糊睡去。
林远把日记合上,轻轻放在窗台边的木盒里。那盒子是用沟泉村最老的一棵槐树芯做的,没上漆,只涂了层蜂蜡,闻着还有点甜香。他手指在盒盖上停了片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屋外风不大,但扬声器群却微微震颤起来,发出低低的嗡鸣,像谁在远处试音。
他走出小屋,沿着石板路往坡下走。春寒未尽,山雾还裹着树梢,湿气扑在脸上,带着泥土与腐叶的气息。菜园里的念禾正弯腰摘蒜苗,蓝布衫袖口卷到肘部,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听见脚步声,她抬头看了眼,嘴角一翘:“又听了一夜?”
“没睡。”林远站在田埂上,“邮件的事……你信吗?”
念禾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从兜里掏出一枚铜铃铛??那是她女儿生前最喜欢的玩具,火场里唯一没烧化的物件。“信。”她说,“你不信?”
林远没答。他知道那声音不可能伪造。不是技术做不到,而是那种语气里的重量,只有经历过深渊的人才懂。那不是录音,是延续。就像雪落进河里,看似消失,实则汇入了流动本身。
“如果真是轮回,”他低声说,“那这次苏醒会比上次更难控制。”
念禾点点头,把铃铛放回口袋。“所以你要写下去。”
“写什么?”
“所有你记得的,听见的,梦见的。不只是故事,是证词。”她望着远处的望音崖,“总得有人留下线索,让下一个守音人知道该往哪儿走。”
林远沉默良久,忽然问:“你觉得‘声渊’到底是什么?”
“不是地方。”念禾蹲下身,捏起一撮黑土,“是记忆的沉积层。我们说过的话,喊过的名,哭过的夜,都被压在地底,一层叠一层,成了另一种地质。它会呼吸,会做梦,也会疼。”
林远心头一震。这说法和《蜂鸟语录》中一段残文惊人吻合:“言为心岩,声作地脉;万语成壤,百音化渊。”他曾以为这是隐喻,现在想来,或许只是古人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描述真相。
他转身欲走,却被念禾叫住。
“阿秀昨天做了个梦。”她说。
林远停下。
“她说她看见一个穿雨衣的小孩,站在废弃车站的月台上,手里攥着半截铅笔,对着空气一遍遍念:‘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为什么不听?’然后铁轨开始震动,整座车站浮了起来,像艘沉船重新升上海面。”
林远闭上眼。他知道那个车站??皖东老线上的青石站,二十年前因地质滑坡整体塌陷,连同当晚值班的调度员和两名滞留旅客一同埋入山体。官方记录里没人幸存,也没人知道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他记得母亲临行前最后一通电话:“远儿,我在查一件旧事。七九年冬,青石站有三个人‘被静默’了。他们的声音……被切掉了。”
当时他不懂,现在懂了。
所谓“被静默”,不是死亡,也不是失踪,而是被“声渊”吞噬。那些不肯闭嘴、坚持说出不该说的话的人,会被系统性抹去声痕,连灵魂都变成养料,喂给那不断扩张的共鸣黑洞。
而孩子手中的铅笔??那是“蜂巢”初代记录工具,用碳粉混合引声膏制成,能在无电环境下捕捉微弱声波。母亲曾教他:“真话太轻,风一吹就散。得用这样的笔,把它钉进石头里。”
林远连夜翻出尘封的档案箱。里面全是母亲遗留的研究资料,多数已泛黄脆裂。他在一堆手稿中找到了一份编号“Q-79”的调查笔记,字迹潦草,夹杂大量声纹图谱与地理坐标。
笔记记载:1979年12月23日,青石站值班主任陈国栋接到紧急通知,称有一列军用货运列车将临时改道经停本站。按规程,他需向区域调度中心确认指令来源。然而三次呼叫均无人应答,电台只传来一段扭曲童谣。当晚十一点零七分,列车未报站名即驶入轨道,车速异常缓慢,车厢全封闭,无编号。
陈国栋试图拦截,却发现通讯完全中断。他启动手动信号灯,却被一股无形力量推倒在地。据其妻后来回忆,那晚他回家时脸色惨白,反复念叨:“他们不让我说……我张嘴,声音就没了……”
第二天清晨,陈家人发现他死于家中,喉部肌肉严重萎缩,法医鉴定为突发性神经退化症。两名当晚值班的实习生也在一周内相继离世,症状相同。而那列神秘列车,从未出现在任何官方运行日志中。
母亲的批注写在页脚:“这不是事故。是‘噬声者’第一次大规模清除行动。目标:阻止某段关键信息外泄。手段:声域封锁+逆向吸收。代价:三人成为‘空腔体’,终生无法发声,死后意识滞留声渊边缘,成为‘回响囚徒’。”
林远的手指微微发抖。他终于明白为何那首童谣会在二十年后重现??它不仅是母亲的呼唤,更是所有被剥夺说话权者的集体哀歌。
他拨通小陈的加密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