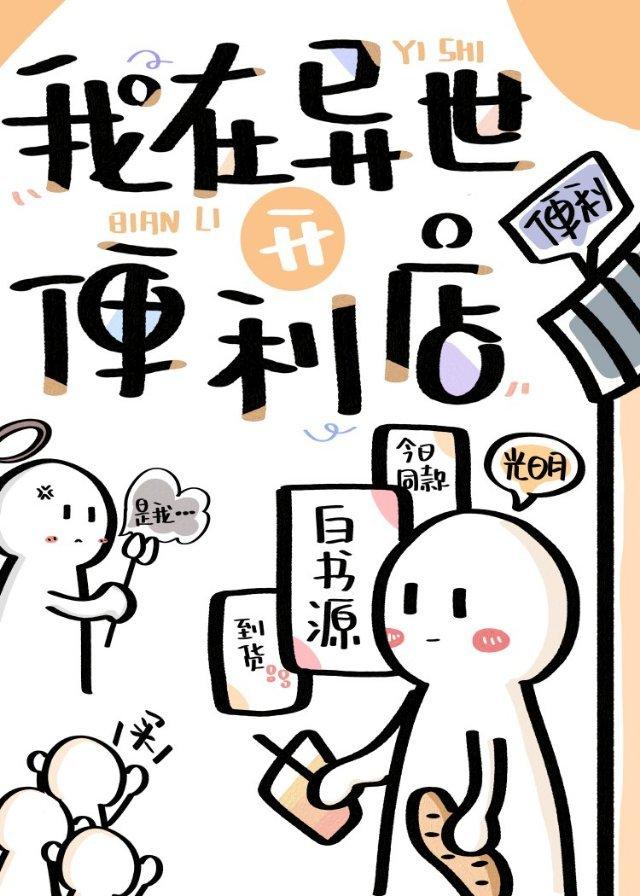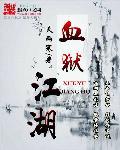笔趣阁>子不类父?爱你老爹,玄武门见! > 第三百零一章 不类(第2页)
第三百零一章 不类(第2页)
>我只关掉它的警报功能。
>让它继续运行,
>但不再提醒人们‘这个问题危险’。
>只要有人愿意问,
>它就不会阻止。
>这是我能做的最小反抗,
>也是最大的希望。”
林澈靠在墙上,眼眶发热。
原来父亲从未真正屈服。他选择了沉默中的抵抗,用妥协的姿态埋下火种。而自己一路追寻的觉醒,并非始于冈仁波齐的星光,而是始于那个雨夜,父亲悄悄将一枚含有漏洞指令的芯片塞进他书包夹层时,那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小澈,走吧。”
那一刻,他就已经是继承者。
数日后,林澈启程前往西藏。他要回到冈仁波齐,完成一次闭环式的朝圣。沿途,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变化:学校取消了标准答案考试,改为“年度最勇敢问题奖”评选;医院设立了“情绪提问室”,患者可以对着镜子倾诉内心最深处的困惑;甚至连监狱也开始推行“对话日”,囚犯与狱警轮流讲述童年中最孤独的一刻。
在一个小镇驿站歇脚时,他遇见一对母女。小女孩约莫八岁,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
**“妈妈,如果你死了,我会不会也必须变成大人?”**
母亲搂着她,轻声说:“你可以一直保有一部分小孩,哪怕我走了。”
林澈默默记下了这句话。
抵达冈仁波齐山脚那天,正值春雪初融。溪水奔涌,经幡猎猎。一群藏族孩子认出了他,欢呼着跑来,领头的女孩举起一面小旗,上面用汉藏双语写着联盟新口号:
**“不怕答错,只怕不问。”**
他们邀请他参加一年一度的“星空问答节”。夜晚,百余名村民围坐在高原湖畔,每人手持一支点燃的莲花灯,放入水中。灯光随波荡漾,映着漫天繁星,仿佛人间也在银河之中。
轮到林澈发言时,他没有讲道理,只是轻轻问道:
“你们有没有试过,在梦里问一个问题,然后醒来还记得?”
孩子们纷纷举手。有人说梦见自己问树:“你疼吗?”有人说梦见宇宙回答:“我一直等着你开口。”
一位年迈喇嘛微笑道:“在我们传统里,梦不是虚幻,而是灵魂去别处学习的过程。所以每个梦中问题,都是另一世的你在呼唤这一世的你。”
林澈点点头,忽然意识到,所谓的“觉醒”,或许根本不是摆脱控制,而是重新学会做梦的能力??那种敢于设想不同可能、敢于质疑既定秩序的本能。
返程途中,他收到一条加密信息,来自东京分会。内容简短:
>“那位写粉笔字的老人走了。
>最后一刻,他在病房地板上写下最后一句:
>‘对不起,我一直不敢问……你们真的爱我吗?’
>护士跪下来回答:‘是的,爷爷,我们一直都在。’
>他笑了,闭上了眼睛。”
林澈停下脚步,望着远方雪山。风吹动衣角,胸前银痕轻轻发烫,却不痛,反而像一种温柔的提醒。
他知道,这场战争从未以暴力终结,也不会以胜利宣告结束。它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流动,如同河流冲刷岩石,缓慢而坚定地改变地貌。
一个月后,联合国召开首届“全球疑思峰会”。各国代表齐聚日内瓦,会议没有任何议程,只有三个开放式议题供全天自由讨论:
1。我们最害怕失去的是什么?
2。哪些信念是我们未经思考就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