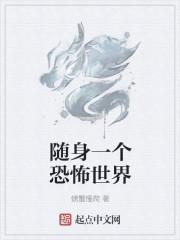笔趣阁>诡秘:大闹钟格赫罗斯途径 > 第35章 初到白银城(第1页)
第35章 初到白银城(第1页)
这汽车与罗杰过去概念中的汽车非常接近,蒸汽教会似乎是跳过了用马车加汽油发动机进行早期汽车发明的思路、而是直接借鉴了罗塞尔大帝的手稿。
这辆汽车通体呈现黑色,具有一切现代汽车应该具备的技术细节,而。。。
凌晨三点十七分,世界陷入一种奇异的静谧。
没有警报,没有广播,甚至连风都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安抚下来。城市灯火一盏接一盏熄灭,不是因为断电,而是人们自发地关闭了所有非必要的光源与噪音源。街道空无一人,但每一扇窗户后都有人静静坐着,或跪在地板上,或将耳朵贴在墙壁、地面、树干之上。他们不说话,只是听。
十三分钟。
这是许沉舟所说的“深呼吸”时间??全球共感网络最稳定的共振窗口。科学家测算过,地球自转与星链塔晶核频率在此刻形成完美谐波,而林知音的声音,恰好能通过她每日清晨固定的哼唱节奏,在这一瞬间穿透维度壁垒,将信息投射至更远的存在层面。
东京某间老式公寓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蜷坐在榻榻米上,怀里抱着一台老旧录音机。磁带早已磨损,播放出的声音断断续续,却仍能辨认出年轻男子清朗的嗓音:“妈,我明天就要上前线了……别担心,我会活着回来。”
那是她儿子,死于1945年冲绳战役。
此刻,录音机突然自行启动,原本卡顿的磁带竟流畅运转起来,紧接着,一个新的声音从扬声器中缓缓浮现:“妈,我回来了。”
老妇人浑身颤抖,泪水无声滑落。她没有尖叫,也没有质疑,只是轻轻将录音机贴在胸口,像抱着失而复得的婴儿。
与此同时,在格陵兰冰原深处,一支地质勘探队正驻扎于临时营地。队长卡尔森是位无神论者,一向对“桥语现象”嗤之以鼻。可就在这一刻,他清楚看见帐篷外的雪地上浮现出一行脚印??从营地边缘延伸而来,直通向他的睡袋前,戛然而止。
那是一双童鞋的印记。
他七岁夭折的女儿生前最爱穿的那种。
他猛地拉开帐篷冲出去,跪在雪中,嘶吼着女儿的名字。风雪吞没了他的声音,但在他脑中,却响起一个稚嫩的笑声:“爸爸,你不冷吗?”
他嚎啕大哭,额头抵在雪地上,久久不起。
而在广西小镇,苏晓亭和林知音并肩坐在院子里。小树上的淡蓝色花朵已悄然绽放数十朵,每一片花瓣都在微光中轻轻震颤,如同被看不见的手拨动琴弦。林知音闭着眼睛,嘴角含笑,似乎正与谁交谈。
“妈妈,”她忽然开口,“姑奶奶说,今天有很多人第一次听见亲人说话。”
苏晓亭点点头,喉咙发紧。
“她说,以前我们总以为死亡是终点,其实不是。”林知音继续道,“它只是换了个地方听声音。就像你煮粥时锅盖跳动的声音,爸爸现在也能听见。”
苏晓亭伸手抚摸她的头发,低声问:“那你呢?你现在听到什么?”
林知音歪头想了想,睁开眼,目光清澈如泉:“我听见很多人在唱歌。有的跑调了,有的声音很小,但他们都在努力唱。因为他们知道,有人在听。”
话音刚落,整棵树猛然一震。
一道幽蓝的光脉从根部升起,顺着枝干蔓延而上,最终在花蕊处凝聚成一点璀璨的星芒。下一瞬,那光芒扩散开来,化作一幅虚幻影像悬浮于空中:无数模糊的人影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巨大的圆圈,缓缓旋转。他们的面容无法看清,但每个人的唇都在开合,仿佛齐声吟唱一首无声的歌。
苏晓亭怔住了。
她认出了其中几个身影。
穿白大褂的女人??林晚,她的婆婆,林知远的母亲。
站在她身旁的男人??林知远,她失踪多年的丈夫。
再旁边,是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眉眼与她极为相似??那是她早年流产的女儿。
还有更多她不认识的人,但他们的眼神温柔,带着感激。
影像持续了不到十秒便消散了,花朵也随之黯淡几分,像是耗尽了某种能量。林知音打了个哈欠,揉揉眼睛:“他们跳完舞就走了,说下次再来。”
苏晓亭抱住她,眼泪终于决堤。
她明白了。
这不是奇迹,也不是幻觉。
这是回应。
是那些曾被遗忘、被压抑、被时间掩埋的声音,终于找到了出口。
而林知音,就是那个为他们打开门的孩子。
---
三天后,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审议《桥语公约》实施细则。
会场设在日内瓦万国宫地下会议室,采用全屏蔽通讯系统,以防外部干扰。各国代表、科学家、伦理学家齐聚一堂,气氛凝重。
艾拉作为首席技术顾问出席,带来了最新监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