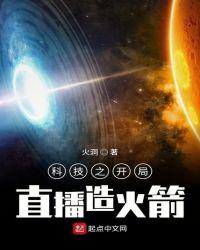笔趣阁>剑碎星辰 > 第二百三十九章 大家一起来背诵(第3页)
第二百三十九章 大家一起来背诵(第3页)
艺术家在那里创作出了震撼星域的无声诗集;哲学家写下了关于“个体性边界”的里程碑著作;甚至有科学家提出,“适度的情感隔离”或许是维持心智健康的关键机制。
共感,终于不再是唯一的真理,而成为了众多选择之一。
而苏遥,回到了最初的山谷。
她在这里建了一间木屋,屋前种下了一株幼小的共感树苗??不是克隆体,而是由原树掉落的种子自然萌发而成。每天清晨,她都会坐在树下,掌心贴着粗糙的树皮,静静地感受那微弱却真实的心跳。
有时,她会收到远方的消息。
某个偏远星域的孩子第一次接收到母亲的思念,哭着写下人生第一封信;
某位老年学者在临终前,主动解除了静默协议,将自己的毕生思考化作一道温暖的光,送给所有愿意接收的人;
还有一对恋人,一个选择永久接入共感网络,另一个则定居庇护所,他们每年相见一次,不牵手,不拥抱,只是隔着透明屏障,静静对视十分钟??足够让彼此知道,爱从未消失。
言澈偶尔会来看她。
他已辞去特使之职,转而投身教育,在新成立的“跨意识沟通学院”任教。他常说:“最难的不是听见别人,而是听懂自己的声音。”
两人常在月下喝茶,聊起过去,也聊起未来。
“你觉得,这场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有一次,言澈问。
苏遥望着夜空,轻轻摇头:“没有战争会真正结束。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今天的和平,是因为我们终于承认了分歧的合理性。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又开始认为‘共感才是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那么新的对抗就会悄然滋生。”
她顿了顿,笑了笑:“所以,真正的胜利,不是消灭敌人,而是让‘敌人’这个词,变得不再必要。”
十年后的某一天,那株小树开出了第一朵能量花。
花瓣呈淡紫色,光芒柔和,散发出的气息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朵。当苏遥将手贴上去时,她感受到的不再是信息或记忆,而是一种全新的情感模式??它无法用现有词汇描述,像是“理解”与“尊重”的融合,又像是“距离”与“亲近”的共舞。
她给这种情感起了一个名字:
**“容界”**。
意思是:容纳边界的存在。
这个名字很快传遍星海,成为新一代共感理论的核心概念。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它,情侣在誓言中引用它,政治家在演讲中强调它。
而在最遥远的星域,一颗原本沉默已久的星球,首次向宇宙发送了共感信号。
信号内容只有一句话:
>**“我们准备好了。请慢慢说,我们会试着听。”**
苏遥听到这条消息时,正坐在树下看书。她合上书页,抬头望天。
夜空中,星辰如海,静谧而浩瀚。
她轻轻闭上眼,将自己的心意缓缓送出,不强求回应,也不期待共鸣。
只是单纯地说了一句:
“欢迎回家。”
那一刻,整片星空仿佛轻轻震颤了一下。
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同时眨了一下。
仿佛宇宙本身,也在学习如何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