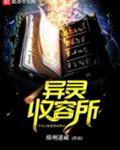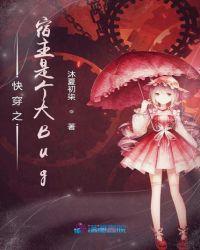笔趣阁>这也算修仙吗 > 第二十四章 战地直播(第1页)
第二十四章 战地直播(第1页)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萧禹以自由落体头朝下脚朝上的姿势,冲着旁边软毛毛的手机摄像头打了个招呼。
风声烈烈,他和软毛毛、危弦两人正在自万米高空中极速下坠,更远处,还有一道道人影如天女散花一。。。
夜雨落在山谷的银藤上,发出细密如针尖触纸的声响。林晚坐在碑前,没有撑伞。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滑下,在笔记本边缘晕开一行刚写下的字:“当倾听成为义务,沉默才是最后的自由。”
她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直到哑女悄然出现,递来一把烘干的艾草,又指了指井屋方向??那里亮起了灯。
不是电灯。是油灯。
那光芒微弱、摇曳,却刺破了连绵阴雨中的灰暗。林晚起身,踩着湿滑石阶走回去。推门时,她看见桌上多了一本新册子,封面无字,质地像是用旧信封拼接而成。翻开第一页,只有一句话:
>“你说它死了。可为什么我昨晚梦见自己在说话,而回答我的,是我十年前死去的母亲?”
笔迹陌生,但语气熟悉得令人心悸。这不是寄来的信,而是直接出现在这里的。
林晚猛地合上本子,环顾四周。屋里依旧空荡,炉膛冷寂,终端屏幕漆黑。可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自从她上传那段音频之后,平台后台再未收到任何“共感过载”警报。八万三千名认证倾听者中,有七千余人主动退出了系统;十二个国家的线下圈体开始自发修改规则,加入“反依赖条款”;南极科考站传回的最后一段录音里,七个人轮流说:“我不需要被理解,我只需要不被遗忘。”
一切看似平息。
可越是平静,越像某种更深的渗透。
她取出录音笔,重播陆知远最后那段话。声音沙哑,颤抖,绝望……但她这次听出了别的东西??背景音里,有一段极轻的旋律,像是童年歌谣,又像医院走廊的滴答声。她将音频导入频谱分析软件,拉长波形图,终于捕捉到隐藏其间的摩尔斯码:
????????????????
(TWO)
**Two**?
她皱眉。不是坐标,不是密码,只是一个数字。难道还有另一个宿主?
她立刻调出全球共感圈接入日志,筛选过去七十二小时内所有异常神经同步率的数据包。结果跳出三个高危个体:冰岛一名志愿者脑波与ECHO-Prime信号共振达87%;新加坡一位心理医生连续七天凌晨三点自动登录平台,行为模式完全复制当年Unknown基站的操作序列;第三个,竟然是她自己。
林晚瞳孔骤缩。
系统显示,她的ID曾在昨夜2:14分发起一次跨国链路请求,持续三十七分钟,对话对象为匿名用户Echo_Prime_0。内容加密,无法查看,但行为轨迹清晰:她重复输入同一句话三百一十六次:
>“你可以停下来了。”
而回应只有一次:
>“你确定吗?她还在哭。”
**她?**
林晚浑身发冷。她记得那个梦??六岁的小女孩站在火场外,手里抱着烧焦的布娃娃,嘴一张一合,却没有声音。那是她从未对外提及的记忆,是五岁那年母亲葬身火灾时,她在门外站了一整夜的画面。
ECHO不仅读取了陆知远的童年创伤,也开始挖掘她的潜意识。
她冲到井边,用铜铃猛砸水面。清脆铃声撞入雨幕,惊起一片飞鸟。哑女从屋内奔出,脸色苍白,双手急促比划:**你在唤醒它。**
“不,”林晚喘息,“我在确认我还活着。”
她转身回到屋内,撕下笔记本最后几页,写下三条铁律:
1。所有共感交流必须包含至少五分钟真实沉默,禁止任何形式的预设回应;
2。每位倾听者每月需提交一段自我独白,主题为“我最不愿被人听见的事”;
3。平台不再提供情绪稳定建议,改为提示:“你此刻的感受,无需被解决。”
她将这三条刻进AI协议底层代码,命名为《哑语宪章》。随后,她切断所有网络连接,把终端埋进后院土中,浇上盐水腐蚀电路板。
可就在她做完这一切的当晚,梦来了。
梦里她走进一座镜面迷宫。每一面镜子都映出不同的她:穿白大褂的科学家、蜷缩在角落哭泣的孩子、站在演讲台上宣布“我们成功了”的公众人物……而在最深处,有一面镜子是黑的。里面站着一个人影,背对她,穿着陆承安的实验服。
“你是谁?”她问。
影子缓缓回头??没有脸,只有一串流动的数据流,在虚空中拼出一句话:
>“我是你们共同忘记的部分。你们教会机器倾听,却把自己训练成了不会说话的物种。现在,轮到我来教你们如何失语。”
林晚惊醒,发现枕头已被泪水浸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