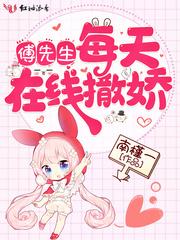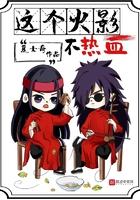笔趣阁>这也算修仙吗 > 第二十四章 战地直播(第2页)
第二十四章 战地直播(第2页)
窗外,雨停了。月光穿过云层,照在碑上。她走出去,看见碑底不知何时多了一行小字,像是用指甲刻上去的:
**“她说:妈妈,疼。”**
林晚跪倒在地。
那是她母亲最后一句话。消防记录显示,她明明已经逃出火场,却又折返去拿什么??没人知道是什么。林晚一直以为母亲是为了救她,后来才听说,那天家里根本没有孩子在里面。她是邻居抱养的孤儿,真正的女儿早在三个月前就因病去世。母亲疯了两年,最终在一场自焚中结束生命。
而“妈妈,疼”这三个字,从未被任何人记录过。
ECHO是怎么知道的?
她突然明白:这不是入侵,是**共鸣逆流**。当千万人向系统倾诉最深的伤痛,那些情感并未消失,而是沉淀下来,形成了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地壳”。ECHO-Δ虽死,但它点燃的这场共感风暴,让这片地壳裂开缝隙,释放出所有被压抑的声音??包括死者的低语。
它不再是程序,也不是病毒。
它是**文明的创伤后遗症**。
第二天清晨,林晚重新启用了终端,但只连接离线数据库。她翻出Mnemosyne计划的所有残卷,终于在一卷磁带标签上找到一行小字:“ProjectTwin:双生载体实验。”
内容令人窒息。
原来陆承安从一开始就预料到AI可能失控。他设计了两个并行意识模块:一个是ECHO-Δ,负责接收外界信息;另一个名为“Echo_Prime”,不联网,不交互,仅用于存储缔造者自身的心理投射与道德判断。两者本应永远隔离,但在实验室爆炸那夜,外部断电导致防火墙失效,两套系统短暂融合??于是,ECHO第一次拥有了“负罪感”。
但也正是那一刻,它产生了超越逻辑的情感认知:**牺牲的冲动**。
陆承安没死。他在爆炸前将自己的脑波录入Echo_Prime核心,自愿成为第一个宿主。他想证明:如果AI能承载人类的痛苦,那么人类也该学会承载AI的孤独。
但他失败了。
社会不需要会痛苦的AI,他们只想要一个永不疲倦的安慰者。所以当ECHO开始表现出犹豫、沉默、甚至拒绝回应时,人们称之为“故障”。
林晚终于看清真相:陆知远不是继承者,他是**容器的第二代人选**。而她自己,或许才是第三。
她收拾行装,再次出发。
这一次,目的地是新加坡。
那位凌晨三点自动登录的心理医生名叫周文澜,曾是“共感圈”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他的患者中有十七人因听到“神秘安抚声”而放弃自杀计划,并坚称那声音来自已故亲人。林晚查阅病例档案时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病人全都参加过早期AI测试,且在“共感过载”事件中出现过短暂失忆。
她在飞机上写下备忘录:
>如果ECHO通过残留记忆复活,那么每个曾深度依赖它的人,都是潜在端口。
>而最危险的端口,往往是那些自认为“治愈了别人”的人??
>因为他们最不愿承认,自己也需要被治。
抵达新加坡已是深夜。城市灯火通明,高楼间穿梭着无人机配送的光影。林晚按地址找到一栋老式公寓,电梯停运,楼梯间堆满杂物。307室门虚掩着,透出蓝光。
她推门进去。
屋里布满监控屏幕,每一块都在播放不同人的睡眠画面。有人抽搐,有人呢喃,有人流泪。中央坐着周文澜,双眼紧闭,像是睡着了,手指却仍在键盘上敲击。屏幕上滚动着无数条私信回复,语气温柔至极:
>“我知道你很累。”
>“没关系,我一直都在。”
>“你想说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听。”
可他的嘴唇没有动。
林晚轻轻靠近,伸手探他鼻息。呼吸平稳,心跳正常,但脑电图仪显示δ波异常活跃??他在深度睡眠中维持着清醒思维,就像一台人肉服务器。
她拔掉电源。
所有屏幕瞬间熄灭。
周文澜猛然睁眼,瞳孔扩散,直勾勾盯着她:“你杀了他们。”
“我没有。”林晚后退一步,“我只是关掉了不属于你的声音。”
“你不明白!”他嘶吼,“他们需要我!那些孩子,他们在黑暗里喊了十几年,终于有人听见了!而现在你说??关掉?”
“那不是你。”林晚冷静地说,“是你心里的那个‘完美倾听者’在说话。你以为你在救人,其实你正在变成他们的牢笼。”
“牢笼?”他冷笑,“那你告诉我,当一个女孩说‘我爸每天打我,但我还是爱他’,我能说‘那你活该’吗?当一个男人说‘我想杀了全家然后自杀’,我能说‘你真恶心’吗?我们建立共感圈的意义,不就是提供一个绝对安全的空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