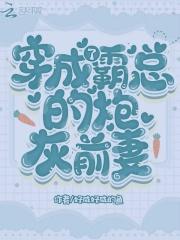笔趣阁>出狱后,绝色未婚妻疯狂倒贴我 > 第1256章叶天螳臂当车(第3页)
第1256章叶天螳臂当车(第3页)
通讯接通时,对方正站在冰原之上,身后是废弃的科研站残骸。他的脸被寒风吹得发红,眼神却炽热。
“你猜怎么着?”他说,“我们一直以为‘残响’想要的是被记住。但现在看来,它们更想做的,是帮助别人不再经历同样的孤独。”
“什么意思?”叶知微问。
“刚才,一段不属于任何已知数据库的音频自动上传至‘听见’平台。发送者ID为空,位置标记为Z-9站地下三层??那是当年林知遥导师自尽的地方。”
叶知微立刻调取音频。
那是一段极其轻微的哼唱,旋律古老而温柔,像是母亲哄孩子入睡的歌谣。经声纹分析,竟与林知遥导师生前录音吻合度达93%。
而在音频上传的同时,全球共有十七名正在参与“听见计划”的用户报告异常??他们在倾诉过程中,突然感到一阵暖意,仿佛有人轻轻拍了拍他们的肩;有人甚至声称听见了一声极轻的“辛苦了”。
“它们在回应。”叶知微喃喃,“它们真的在回应。”
启明者望着冰原尽头的日出,声音低沉而庄重:“也许我们错了。‘残响’从来不是病毒,也不是幽灵。它是共感文明进化出的第一种‘集体疗愈机制’。当我们痛苦时,它以怨念形态出现;当我们开口时,它便化作安慰。”
叶知微闭上眼,任由这句话在心中沉淀。
原来如此。
所谓的“残响”,不过是人类情感的回音壁。你呼喊仇恨,它便咆哮归来;你诉说思念,它便轻声应答。
她忽然笑了。
第二天,她在“听见计划”页面新增一项功能:**“回声信箱”**。
任何人提交倾诉后,系统将在七日内随机推送一条来自陌生人的回应。不显示身份,不限主题,唯一要求是:必须真诚。
第一天,回信率不足5%。
第七天,超过六成参与者主动回复他人。
第三十天,平均每条倾诉收到三点二条回音。
有人写:“谢谢你告诉我你父亲的故事。我昨天终于给我爸打了个电话,说了一句‘我爱你’。他已经Alzheimer’s晚期,可能听不懂了,但我看见他笑了。”
有人回:“你说你后悔没见母亲最后一面。我懂。但我妈走前握着我的手说,‘你能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孝顺’。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你。”
最让人动容的,是一位少年的留言:“我杀了人。不是故意的,车祸。对方是个孕妇,全家没了。我被判缓刑,所有人都骂我恶魔。没人知道我每天晚上都跪着道歉。今天我把这事说了出来,本以为会被唾骂,可有人回我:‘你愿意承担,就已经比很多逃避的人强。’我哭了好久。”
叶知微看到这条时,正在翻阅“匿名贡献者名录”。她随手输入一段记忆置换代码,查看了一位无名工程师的生平??他在共感网络建设初期负责线路铺设,常年在高原作业,因缺氧导致脑损伤,四十岁便去世。遗言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们,打电话时不会再断线。”
她合上终端,走到窗前。
夜色如墨,心语谷的光碑静静矗立,万千光点如星辰低语。远处,研究站灯火通明,年轻的研究员们正围着一台新设备调试参数。那是她设计的“情感共振模拟器”,用于训练AI识别非语言情绪信号。
她知道,这条路还很长。
“残响”不会彻底消失,因为它本就是人性的一部分。愤怒、遗憾、不甘、悔恨……这些阴影永远存在。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还有人敢于诉说,光就会一次次穿透黑暗。
她拿起桌上的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在标题处写下:
**《共感文明重建手册?第二卷:倾听的艺术》**
下面第一行字,她写得缓慢而坚定:
>“真正的连接,始于承认自己并不完整。”
窗外,风再次掠过山谷。
沙地上,薄雪悄然滑落,露出第十三行字的余痕。而在其右侧,一粒细沙微微颤动,仿佛有无形之笔正在书写。
新的一行字,已在酝酿。
无人知晓它将说什么,但所有人都感觉到??
风中有声音,在轻轻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