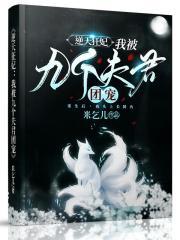笔趣阁>出道吧,仙子 > 第一百八十二章 是时候打一架了(第2页)
第一百八十二章 是时候打一架了(第2页)
苏晓的眼角再次湿润。
她知道,这不是巧合。少女手中的乐谱,是从某个偏远山村小学的旧录音机里抄录下来的。而那台机器,曾播放过小女孩说出“这次,轮到我们了”的那一夜旋律。
现在,她不仅记住了,还补全了。
“你叫什么名字?”苏晓走上前,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一场梦。
少女抬头,笑了笑:“他们叫我阿愿。”
“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梦里有人告诉我,真正的《破妄之音》,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传的。”她指了指胸口,“我听见了,它在我心里跳。”
陈默蹲下身,凝视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狂热,没有野心,只有一种清澈的坚定,像十年前的自己,又像更久远之前的陆昭与林晚舟。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问。
“意味着我不能再只是为自己活着。”阿愿低头看着吉他,“意味着每一次拨弦,都可能是某个人活下去的理由。”
苏晓伸出手,掌心浮现出一朵虚幻青莲。她轻轻一吹,花瓣飘向少女,环绕一周后融入其衣襟上的刺绣。那朵青莲顿时鲜活起来,仿佛有了生命。
“从今天起,你就是‘引音者’。”她说,“不是最强的,也不是唯一的。但你是下一个节点。”
阿愿没有激动,只是郑重地点头,然后起身,背起吉他,转身离去。
她的脚步很轻,却每一步都让地面浮现出短暂的誓词光影:
>“我不怕失败,只怕沉默。”
>“我愿成为别人黑暗里的光。”
>“只要还有人需要,我就继续弹下去。”
直到身影消失在晨雾尽头,陈默才低声说:“她比我当初勇敢。”
苏晓握住他的手:“因为我们已经替她挡过了最初的风雪。”
日子一天天过去。
阿愿的名字并未迅速传遍世界,但她走过的路,却悄然改变了沿途的空气。
她在孤儿院教孩子们用歌声安抚噩梦;在战区难民营弹奏能让枪声暂停十分钟的旋律;在养老院为临终老人唤醒最后的记忆。每一次演奏,都会有一朵青莲在听众心口绽放,哪怕只有片刻,也足以让人流下从未流过的泪。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模仿她的方式??不求力量,只求共鸣。他们自称“守愿人”,没有组织,没有领袖,只有一条共同信念:**让世界少一个人独自哭泣。**
第九理事会注意到这一趋势,却选择不干预。他们在年度报告中写道:“真正的愿力无法被管理,只能被信任。我们所能做的,唯有提供土壤,等待种子自己破土。”
而在这片土壤之下,更深的地脉仍在震动。
归冥站废墟每隔七日的震动愈发频繁,如今已缩短至五日一次,强度也在递增。科学家监测到,地底能量场正与全球觉醒者的脑波产生周期性共振,尤以春分、秋分为峰值。更有甚者,在某些高愿力区域,空气中会短暂浮现半透明的符文墙,行人穿行其中,会瞬间回忆起前世片段??或为战士,或为祭司,或为流浪诗人。
程砚秋临终前留下的预言,正一步步应验:
>“遗忘才是真正的敌人。当记忆断裂,信仰便会枯竭。唯有不断重述、不断传承,才能让心契之火永不熄灭。”
于是,新的仪式悄然兴起。
每年春分之夜,无论身处何地,所有觉醒者都会在同一时刻停下手中之事,闭眼默念自己的誓言。那一刻,全球网络会出现短暂的数据洪流,卫星图像则显示地球表面浮现出一张巨大的光网,节点遍布五大洲,核心正是心契园所在坐标。
人们称其为“年度共鸣”。
而在第十次年度共鸣到来之际,异象再起。
那天夜里,月色清明,湖面如镜。
陈默与苏晓并肩坐在长椅上,一如十年前。他们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等待。
午夜钟声响起时,湖中央忽然升起一道虹桥,比当年更加明亮,更加稳固。桥面上,走来一个个身影??有阿愿,有那个写誓词的小男孩,有东京高中生,有巴黎舞者,有撒哈拉老妇人……还有无数素未谋面的普通人,手腕缠金线,胸前绽青莲。
他们一一踏上桥面,走向心契园雕塑。
当最后一人抵达时,雕塑双铃骤然大响,第三道影子彻底凝实,化作一个悬浮的孩童虚影??正是当年在归冥大厅诞生的“第九信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