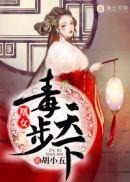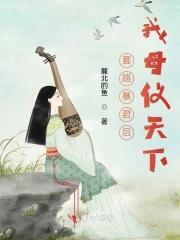笔趣阁>凤谋金台 > 100110(第23页)
100110(第23页)
“你详细说说。”李鸾徽眉头微挑。
冯知节翻开手中军报,沉声道:“凉州、西域数地,近日屡有异动。尤其是北魏旧王族与隋之后裔,在地方仍有土地、宗族、门生故旧。他们得知我朝改制意图废除北魏、隋之正统,极为不满,密谋聚众,勾结江湖义士。”
“近日边关传来密报,有人自称‘魏王再世’,在民间招揽死士,暗立旌旗。西凉一带,有百姓聚众呼应,已有兵丁失踪。”
李鸾徽的脸色冷了下来,甚至觉得有些好笑,“魏王再世?这些余孽还敢作妖?”
李文韬拱手道:“圣上,若真有人以’正统’之名号聚众,恐怕不仅是边地军情,更是朝纲震荡。”
“更有江湖人物——”他顿了顿,目光掠过在座众臣,“某些流派门主,与旧族通好甚密。今朝改制,必损其既得之利,或明或暗,皆有抵触。”
陆明川也开口:“臣近日巡视京中文馆,发现部分藏书馆、学宫,仍沿用旧朝礼制编章,拒绝启用新礼。学者抵制新律,言朝廷欲断文化之源,断民心之根。”
李鸾徽眼神愈发冷峻,端起茶盏抿了一口,问道:“你们的意思,是改不得了?”
“臣不敢。”冯知节躬身,“臣之意是,需谨慎推进,步步为营。”
“步步为营,步步为营……”圣上低声念着,忽地将茶盏重重一放,脆响一声,让众人皆一惊。
“魏孽余魂,隋后作乱,皆因旧制苟存,土壤未除。”李鸾徽站起身来,衣袍随之飞扬,声音如铁,“如今朝纲既改,若犹豫不决,只会养虎为患。”
“朕意已决。”他目光如刃,“改制继续,沿边旧族,凡有异动者,严惩不贷!”
李鸾徽低头,拱手道:“是。”
“凉州调兵三千,西域调兵五千,由兵部统一调配。必要时与兵部、御史台联合办案,借征伐之名清理旧族残余。”
李鸾徽说得极快,像是在念一篇早已写好的策论。
牛和德接道:“臣建议,可设一‘改制督司’,由礼部、户部、御史台三方共同参与,分赴各地,监督各郡官员推行改制进度,并密察其是否有旧族之私通。”
圣上点头:“此议可行。牛卿你起草章程,三日之内交朕御览。”
他望向殿内,“凡反对者,不必劝谏,速速退位。改制一道,不容含糊。”
李文韬躬身而立。
“臣请愿入‘改制督司’,为朝纲清浊,为大唐清根本。”他高声道。
“准。”
李鸾徽终于坐下,轻轻一叹,“诸卿,这改制,动的是根,不是枝。枝折了,明年还会生;根坏了,一棵树都要烂。”
众臣闻言,皆低首拱手。
这场会议,自日初开至申时尽,整整五个时辰,众人几乎未起席。
但无一人敢喊疲累。
会议散后,热风吹过,牛和德与李文韬并肩而行,两人俱是沉默。
走至殿外,牛和德忽然低声道:“圣上已下决心,可你我心里都明白,改制若真推进下去,不知多少人要掉脑袋。”
李文韬平静回应:“但这一步,总得有人走。”
阳光斜照下来,御道上落日如血,将琉璃瓦染出一层金红。
六部大臣们鱼贯而出,而秦斯礼逆着人流走进宫中。
他应召前来,天色虽晚,却仍步履从容。只是眉宇间难掩疲色,自朝中风波至今,他便少有歇息之日。
含元殿内静谧如水,光线幽暗,长灯将殿柱的影子拉得极长。
殿门未闭,微风吹拂,帘幔轻颤。
只是殿外空地上,跪着一人。他走了几步,只见一女官跪伏在地,发髻凌乱,鬓边血迹未干,显然是刚受过杖责。
秦斯礼目光一顿,认出那人乃是礼部兼史馆记录的史官杨思蕊,素以才华出众、性情刚烈著称。
如今却狼狈不堪,身侧杖棍未收,血渍尚新。
她低着头,不见脸色,身形微颤,显是疼痛难当,却咬紧牙关未出一声。
秦斯礼移开了目光,什么也没说,只走进了含元殿内,跪下请安:“臣秦斯礼,奉召觐见。”
高座之上,李鸾徽并未即刻开口,只缓缓合上手中奏折,神情淡然地望着他,语气却转向另一种沉静:“凉州出事了。”
这句话平静如水,却让殿内气温骤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