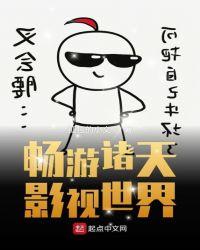笔趣阁>掌门怀孕,关我一个杂役什么事 > 第444章 林陌 搞他家人(第2页)
第444章 林陌 搞他家人(第2页)
“我不是叛徒!”
“我儿子才十六岁啊!”
“那天晚上他们把书烧了,整整三天三夜!”
小葵的手不停,一笔一划勾勒出他们的脸。每一幅面孔成型,纸上就浮现出对应的遗言片段,自动汇入羊皮卷。可随着画面深入,她的呼吸越来越浅,瞳孔逐渐扩散,嘴角溢出血丝。
“快停下!”素言扑上去想拉她。
“别碰她!”昭穗厉喝,“这是契约仪式,中断只会让她魂飞魄散!”
果然,就在素言收手瞬间,小葵猛然抬头,双眼竟泛起青铜色光泽。她开口说话,声音却非一人,而是层层叠叠,似有千百人在齐诵:
>“吾等皆曾开口,故遭剜舌;
>吾等皆曾执笔,故断指焚稿;
>吾等皆曾教子识字,故灭门绝嗣。
>今以残魂寄此画卷,求一见天光,求一句公道。”
全场寂静。
随后,整座回音谷的铜铃齐鸣,不只是谷内,千里之外的共感学堂、历史清源司分部、甚至边陲戍所的守夜人,全都听见了这段话。许多人当场跪倒,泪流满面。
小葵缓缓倒下,昏迷前最后一句话是:“青萝……终于走到对岸了。”
七日后,她醒来。
记忆模糊,却不痛苦。她发现自己能听懂风吹树叶的节奏,那是三百年前某个女童背诵《千字文》的残响;她能在雨滴落地时看见幻影,那是被焚书院最后一位先生写在墙上的“民可明,不可欺”。
她成了“通语者”??既非纯粹共感者,也非传统绘忆师,而是介于语言与图像之间的桥梁。她的画不再只是静态影像,而是会动、会发声、会流泪的记忆活体。
与此同时,《未言录》恢复平静,冰封加固,但人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安宁。
因为新的声音仍在涌现。
南方某渔村,一名老渔民在修补渔网时突然停手,喃喃道:“我不是在补网,我在记名字。”他写下十二个陌生姓名,附注:“庚戌年四月十三,海难非天灾,乃官船强征民船运私盐,遇风暴沉没。幸存三人,全被灭口。”经考证,此事确有档案记载,但原文件标注“永久封存”。
西北驿站,一位退休邮差临终前将毕生收藏的信件交给孙子:“这些信,当年都没送到。不是丢了,是被人挑出来烧了。理由:‘内容可能引发不安’。”其中一封竟是三十年前失踪诗人的绝笔:“若我的诗只能藏于地下,请让它成为种子。”
更令人震惊的是,京城皇宫旧档房在修缮时,意外发现一间密室,内有一面“静音墙”,墙上嵌满银针,每根针尖都沾着干涸血迹。专家解读后确认:这是“缄口律”执行工具,用于刺穿异议者的声带神经,使其终生不能清晰发音。墙上还刻着一句话:
>“宁杀百人,不放一言。”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皇帝亲自下诏道歉,并宣布设立“言语赎罪日”,每年春分全国默哀三分钟,纪念所有因言获罪者。
然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这一年夏至,钦差大臣携调查团重返言归坊遗址,进行深度挖掘。在地下十八丈处,发现一座完整祭坛,中央正是那根舌形石柱,上面新增了数百个名字??全是近年来参与“拾音行动”的成员。
包括昭穗。
“这是诅咒标记。”默老师抚摸石柱,声音冰冷,“凡是触碰禁忌之人,都会被‘静默工程’的残余力量记录在案。他们虽已覆灭,但机制仍在运转,如同毒蛇断头后尾部仍会抽搐。”
昭穗看着自己的名字,反而笑了:“很好。至少证明我们动了他们的根。”
当晚,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荒原上,面前是无数张嘴,全都闭着,嘴唇缝着银线。忽然,小葵从远处走来,手中拿着一幅画。她将画展开,画中是今日的回音谷,阳光明媚,孩子们在铜镜前大声朗读自己写的诗。
那些闭着的嘴,开始一根根崩断银线。
第二天清晨,昭穗召集所有核心成员,宣布成立“启舌盟”??一个跨地域、跨阶层的民间组织,旨在系统性唤醒被遗忘的真相。他们不再局限于拾取记忆,而是主动寻找沉默之地,点燃言语火种。
行动代号:“花开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