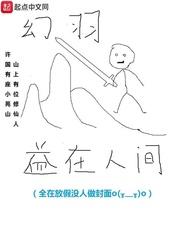笔趣阁>我靠摄政王八卦发家致富 > 往事再提(第2页)
往事再提(第2页)
话音刚落,暗处有一人上前来,一把提出那人的领口,闪着寒光的刀尖对准了脖颈,正要下手却被拦住,“罢了,不必。自有人料理!”
回来禀报的死士被拖着领子带了出去,却不敢发出一句惊恐的叫声。
大人站在一地的碎瓷片中,喃喃道:“如今只有阿罗汉能解此局了,否则你我,都没有好下场……”
“大人,现在该怎么办?”
焦躁的气氛在屋子里四处弥漫,此人压低声音道:“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这时,一个仆役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跪地问安后,双手奉上一封沾血的信,仔细看去他的胳膊上透出殷红的血色,他忍着痛道:“大人,有信。”
信封被一点点拆开,里面只写了短短一行字,“此地,阿罗汉,十日,三千两。”
那人一把攥紧了信纸,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真是嚣张……”
马车到王府后,顾涟初就钻进了自己房间里,快到截稿日子,他坐在窗前构思了整整一晚,要写什么。
想不出来时,就看着卧房亮着的灯发呆。
夜已经深了,李冕突然推开了窗,看见他还半开着窗坐在桌前,问道:“怎么还不就寝。”
顾涟初咬着笔头,“还不困。”
两人说了几句话就道了夜安,顾涟初继续构思着自己的李冕八卦。
脑袋中又浮现出金钟的故事来。
看着自己的父亲为兄长制作精美的金钟,小李冕又是什么心情呢?
他是怎么从那样一个小可怜长成如今这个样子的?
思前想后,顾涟初还是没有将这个故事写在八卦中,而是想起了李冕剿匪的功绩。
整整一夜,顾涟初伏案写作,一直到天光微亮,仍旧没有停歇,甚至有越写越精神的感觉,直到李冕卧房传来声音,他才迟迟地踏上床,准备去睡觉。
等到他睡醒,王府又只剩下他与叶崇石两人,连苏云书都接了诊出门了。
顾涟初先跑到茶楼买了卤牛肉和叫花鸡,再来了整整一坛上好的酒,这酒是最近京城最时兴的松花酒,足足要五两银子,可给顾涟初心疼坏了。
他提着吃食找到叶崇石,这人王爷一不在就躲在门房里享清闲,二郎腿翘着躺在床上,手里还翻着什么话本。
顾涟初提溜着油纸包在他眼前晃了一圈儿,从床边冒出来:“喝点儿?”
叶崇石书一扔,直接一个倦鸟投林抱住顾涟初的腰:“顾哥!大好人!”
两个人就在门房的小桌子上,开吃了。虽然是白日饮酒,但是今日天阴,没有晴色。开着窗风灌进来的时候,喝酒又像取暖一样,没有那么不合时宜了。
两个人一口肉一口酒聊着天儿。
叶崇石跟叶崇玉不愧是两兄弟,简直是如出一辙的活泼,但又是不同风格的话多。
叶崇玉总是带着几分混不吝,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除了王爷没有外号以外,全被他揶揄了个遍。
动辄叫他小狐狸、刺客,叫小石头,叫彤彤,一个大男人偶尔还会撒娇耍痴。
但是叶崇石则是带着几分少年的天真。
顾涟初给他倒上酒,道:“你和你哥真的很像。”
叶崇石得意洋洋地挑眉,“那当然,我哥将我一手带大的。”
顾涟初笑了一下,“将你带得这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