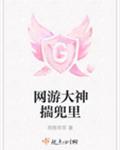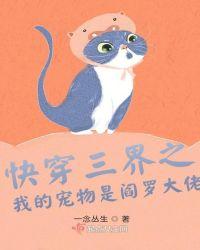笔趣阁>我在现代留过学 > 第一千零七十六章 立项(第1页)
第一千零七十六章 立项(第1页)
很快,礼部选定的吉时便到了。
随着正安之乐,进入一个新的节奏,隆隆鼓声,伴随着清脆的击罄之声。
恢弘庄严,肃穆堂堂。
琼林宴开始了。
新科进士们,在礼部尚书王存的引领下,从琼林。。。
>“你说得对,孩子。说话不该死。”
他吓得往后一缩,椅子吱呀作响。母亲在隔壁咳嗽两声:“阿禾,天还没亮就写什么?快睡吧。”
“娘,我……我听见有人说话。”
“鬼话!这大清早的,哪来的人?”
阿禾没再应声,只盯着那行字。它慢慢淡去,如同被风吹散的烟,但纸上残留的温度却久久不退。他伸手摸了摸,竟觉得那地方像有心跳。
与此同时,京城国子监废墟中,柳莺儿正跪坐在残垣断壁之间,面前摊着一本用碎布拼成的册子??那是她三个月来走访各地、收集口述而成的《默语录》。每一页都记录着一个曾因言获罪者的临终遗言:有的是临刑前塞进狱卒鞋里的纸条,有的是刻在牢房砖缝中的指甲痕,还有的,是家人多年后才从疯癫亲人口中听出的呓语。
她翻到最新一页,上面写着莆田一位老塾师的回忆:“我教了一辈子书,最得意的学生叫陈文昭。他文章写得好,说‘民瘼如疮,不可讳疾’。结果春闱放榜,名字被划去,说是‘心怀怨望’。后来听说他在流放路上跳了崖。我从此再也不讲孟子。”
笔尖顿住。柳莺儿抬眼望向祭坛方向??那面由十三口井镇魂铃合铸的青铜镜仍立在那里,表面布满裂纹,却不再反光。自那一夜光柱冲天之后,它便彻底沉寂,仿佛耗尽了所有力量。
“真的结束了吗?”她轻声问。
身后传来脚步声。崔元朗披着旧袍走来,手里提着一只陶壶。“昨夜又有三座村子自发立碑。”他将壶放下,倒出一碗热汤,“说是受了莆田启发,把祖上被贬、被杀、被污名的先人名字都刻了上去。有个七岁娃娃,亲手在他爹坟前写了‘冤’字。”
柳莺儿接过碗,却没有喝。“可你也知道,朝廷已经开始压了。昨日开封府下令,禁止民间私设‘忆堂’,说是有煽动之嫌;礼部重申‘非经核准,不得刊印史论’。连《罪己实录》的抄本都被限制流通,只准士大夫阅览。”
崔元朗冷笑一声:“他们怕的不是过去,是现在。一旦人人都敢说真话,谁还信他们编的故事?”
“可百姓呢?”柳莺儿望着远处炊烟袅袅的民居,“他们会记得多久?十年?二十年?等这一代人都死了,这些事会不会又变成传说?”
风起,吹动残破的幡旗。一片焦黄的纸片从废墟中飘起,打着旋落在她膝上。她拾起一看,竟是半页科考试卷,墨迹模糊,但仍能辨认出一句:
>“若我是天子,第一道诏书便是:许人言。”
她怔住。这字迹她认得??是耶律琚年轻时的手笔。据说他曾参加过一次科考,因策论直斥宰相专权而被除名,试卷也被焚毁。没想到,竟有一角残片留存至今。
“他还活着吗?”她忽然问。
崔元朗沉默片刻:“没人知道。观星台那晚之后,他就消失了。有人说他去了西域,有人说他入山修道,还有人说……他化作了白鹰,飞进了云里。”
柳莺儿摇头:“我不信他会走。他不是为了逃命才做这一切的。”
“所以他还在某处点灯。”崔元朗低声道,“就像那个孩子一样。”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马蹄急响。甘兰进骑马而来,衣襟染尘,脸上带着罕见的惊色。“西北急报!”他翻身下马,声音沙哑,“凉州那边……出事了。”
众人神色一凛。
“养童坊遗址……又开了。”
“什么?”柳莺儿猛地站起,“不是已经封死了吗?官府派兵驻守,还立了‘永禁之地’碑!”
“碑被人推倒了。”甘兰进喘息道,“昨夜三更,整片废墟突然震动,地下冒出黑雾,形状像人,却不伤人,只是围着原址转圈,嘴里反复念一句话:‘我们没烧完。’等到天亮,雾散了,地上多了三千具白骨,排列整齐,每一具胸前都压着一块石板,上面刻着名字、籍贯、死亡年月……全是当年失踪的孩子。”
崔元朗脸色铁青:“怎么可能?那些尸骨早该化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