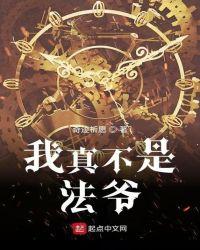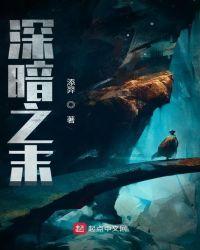笔趣阁>原神,长枪依旧 > 第二千二百九十五章 前往须弥二合一(第3页)
第二千二百九十五章 前往须弥二合一(第3页)
>“即日起,取消‘言论风险评估’制度。凡属合理质疑,皆视为建设性意见处理。”
数日后,蒙德城外山坡上,温迪倚树饮酒,琴团长坐在身旁翻阅最新一期《自由问答报》。
“嘿,上面登了我的诗。”吟游诗人晃着酒瓶笑道,“题目叫《致未来的酒保》,讲的是如果有一天所有人都不敢质疑酒的价格,那醉的就不只是身体了。”
琴忍不住笑出声:“你居然写社会评论了?”
“没办法,”温迪耸肩,“孩子们都在学着提问,我总不能还只会唱情歌吧?”
他仰头饮尽残酒,望着蓝天悠悠道:“其实吧,我一直知道,风带来的不只是歌声,还有无数未曾出口的问题。它们飘在空气里,藏在树叶摩擦的沙响中,等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琴合上报刊,轻声问:“你觉得……我们会一直保持这样吗?”
“不会。”温迪答得干脆,“一定会有人怀念过去的‘安稳’,想要关上门窗,说‘别闹了,就这样挺好’。但只要还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对,还可以更好’,风就会再次吹进来。”
他站起身,拍去尘土:“而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世界??不必完美,但永远留有一扇未关的窗。”
同一时刻,雪山深处的小屋里,少年教师正批改作业。桌上油灯昏黄,墙上影子摇晃。学生们交来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篇篇《我的困惑日记》。
一个孩子写道:“我家狗死了,妈妈说它去了天上。可我在书上看到动物没有灵魂。那它到底去哪儿了?我不想骗自己说它很快乐,因为我想它。”
另一个写道:“班长帮我打架,我觉得感激,可老师说暴力不对。那到底是该感谢他,还是批评他?如果两个都是对的,为什么它们会打架?”
少年一页页读着,眼眶渐湿。
他翻开自己的《未完成的问答录》,在最新一页写下:
>“教育的目的,不是制造顺从的回声,而是培育独立的疑问。
>当孩子学会怀疑课本,而非怀疑自己时,光明才会真正降临。”
合上本子,他抬头望向窗外。夜空中,思兰的种子随风飘舞,如同亿万微小星辰,照亮了整片山谷。
而在某间医院病房里,一名垂暮老人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床边坐着他的孙子,手里捧着一本破旧笔记本。
“爷爷,这是你在渔船上写的吗?”
老人艰难地点点头。
“这里面说,海里的门还会开,只要有人还记得要问‘为什么’……是真的吗?”
老人努力挤出一丝微笑,用尽力气说出最后一句话:
>“只要……还有人在问……它就从来……没有真正关闭。”
话音落下,监护仪发出长鸣。
孙子低头看着那本焦边笔记本,泪水滴落在“第三页”上。奇异的是,那页原本空白的地方,竟缓缓浮现出新的一行字:
>“你问了吗?”
与此同时,全球各地数十万人在同一瞬间做了同一个梦??他们站在一片无垠海边,面前是那扇青铜巨门。门缝微启,光流涌动,耳边响起古老而温柔的低语:
>“欢迎回来。这一次,请带着问题进来。”
黎明将至,晨雾弥漫。
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一朵思兰悄然绽放,花瓣上浮动着两个字,宛若心跳:
**“为什么?”**
风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