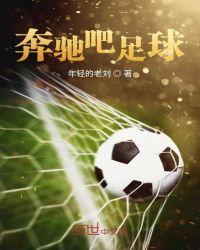笔趣阁>我是如何当神豪的 > 第一千五百五十二章 聊风声(第1页)
第一千五百五十二章 聊风声(第1页)
井高和万父见面的地点在一楼的一间小客厅,其间陈设雅致。
万父的容貌和万菲菲相似,四五十岁的年龄,依稀可见年轻时的英俊。穿着白衬衣、西裤,带着一副体制内工作的气质,却并无上位者的压迫感。
这。。。
高铁驶入敦煌站时,天边正泛起一层淡淡的橙红。井高拖着行李箱走出站台,风里裹着沙粒的微响,像某种古老语言的低语。他没打伞,任那干燥而粗粝的风吹过脸颊,吹进衣领。三年前他来过一次,那时清霜刚接手壁画修复项目,两人在莫高窟外的胡杨林里走了很久,谁也没说话。如今再踏这片土地,脚底生出一种奇异的踏实感,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时间的纹路上。
清霜早就在站口等他,穿着浅灰冲锋衣,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脸上有轻微晒痕,眼神却比从前更亮。她没笑,只是看着他走近,然后说:“你迟到了七分钟。”
“列车晚点。”他解释。
“我知道。”她终于笑了,“我在监控里看了半小时。”
他们并肩走向研究院宿舍区的路上,谁都没提过去,也不谈未来,只聊些琐碎事:哪条路最近被流沙掩了,食堂新来的厨师炒菜太咸,隔壁组的小赵昨天因为颜料配比失误差点毁了一角飞天裙裾。井高听着,频频点头,心里却清楚??这些日常的絮语,是她给予他的接纳仪式。
第二天清晨六点,他准时出现在第156窟外。清霜已经在洞窟门口架好设备,助手们正调试灯光梯架。她回头看他一眼:“别靠太近,呼吸会影响壁画湿度。”
“明白。”他退后两步,静静站着。
阳光透过遮光帘斜切进来,落在南壁那幅仕女图上。千年的矿物颜料在特定角度下忽然苏醒,朱砂红、石青蓝、金粉勾边,层层叠叠如云霞流转。一位仕女执扇而立,眉心一点花钿,唇角微扬,似笑非笑。井高屏住呼吸??这不是画,这是活过来的人。
“我们用了三个月才清理掉最表层的霉斑。”清霜低声说,“唐代工匠用蛋清调和颜料,所以色彩能留存这么久。但每一笔修补,都必须比发丝还轻。”
“你们怎么知道原来是什么颜色?”
“靠比对邻近未损区域,还有文献记载。”她指了指工作台上的笔记本,“你看这个纹样,我们在吐鲁番出土的一块残布上找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图案。”
他走近细看,忽然发现仕女耳坠上有个极小的符号,像篆书又似梵文。“这是什么?”
清霜眼神一闪:“这是我们最近才发现的。初步判断,可能是画师的名字缩写,也可能是供养人家族印记。”
“能查出来吗?”
“也许。”她顿了顿,“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不是无名之辈。哪怕一千四百年后,仍有人愿意为她费尽心思。”
那一刻,井高忽然明白了自己为何而来。他不是为了见证奇迹,而是为了确认:有些东西,值得被长久地记住。
中午吃饭时,他问清霜:“你后悔离开北京吗?”
她夹了一筷子凉拌骆驼刺:“你说呢?当年你在董事会上拍桌子说要投三百万做‘萤火计划’的时候,多少人笑你傻。可现在呢?”
“可你现在每天面对的是剥落的壁画,不是掌声。”
“但每一笔修复,都是对抗遗忘。”她直视他,“你不也是?你建帐篷图书馆、推‘她创空间’,不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不被忘记?”
饭后回到宿舍,他收到热热的消息:【《看不见的女人》成都展首日观众破万,有个小女孩在互动墙写了“妈妈上班回来很累,但我没说过谢谢”,被网友疯转。】
他回了个笑脸,又补了一句:【告诉李曼,她妈妈要是来了,安排VIP通道。】
当晚,清霜带他去了藏经洞陈列馆。灯光昏黄,玻璃柜中陈列着残卷、木牍、写经。她在一册泛黄的《妙法莲华经》前停下:“这是唐代一个女供养人捐的,名字叫阿阮。她在题记里写:‘愿我来世,得菩提时,光照幽冥。’”
“幽冥?”
“她说的不是地狱,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清霜轻声说,“就像你做的‘她创空间’,不也是照亮幽冥吗?”
他沉默良久,忽然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付出。可今天我才懂,真正被救赎的,是我。”
“因为你终于学会了‘看见’。”她望着他,“以前你眼里只有目标、数字、结果。现在,你能看见一片叶子怎么长出来,一个女人为什么流泪,一幅画背后有多少双手在守护。”
他苦笑:“代价不小。”
“但值得。”
第三天,他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在专业指导下尝试参与最基础的除尘工作。指尖颤抖,动作僵硬,被师傅训了三次“太重”。清霜在一旁记录数据,头也不抬地说:“你以为当神豪就能随便碰千年文物?在这里,钱买不到资格。”
“我知道。”他擦去额角汗珠,“所以我来学。”
傍晚,他们坐在研究院后山的土坡上看日落。远处鸣沙山轮廓渐暗,月牙泉像一枚银钉嵌在沙海之中。清霜忽然说:“你知道吗?唐代画工大多是匿名的。他们画完就走,不留名,不求赏。但他们相信,美本身就有意义。”
“就像你。”
“也像你。”她侧头看他,“你不再需要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井高了,对吧?”
他点点头:“以前我觉得,被人记住才是成功。现在我觉得,能让别人被记住,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