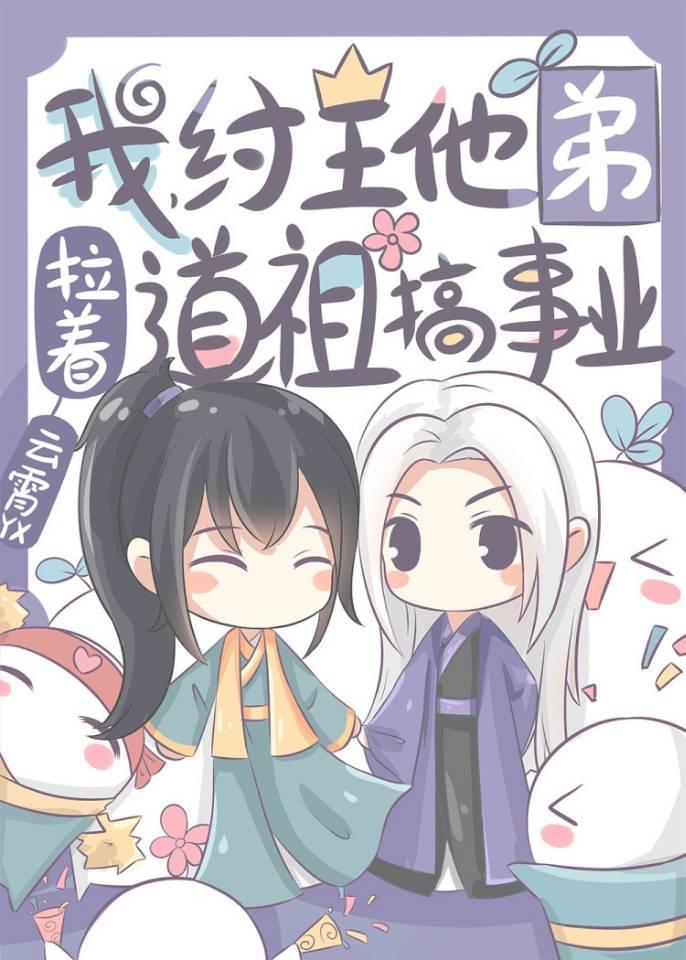笔趣阁>我是如何当神豪的 > 第一千五百五十二章 聊风声(第2页)
第一千五百五十二章 聊风声(第2页)
手机震动,是林薇的消息:【孩子会叫“妈妈”了,第一次没喊错。谢谢你那天在医院陪我说那么久的话。】
他回复:【该谢的是我,你教会我什么叫坚持。】
清霜瞥见屏幕,轻笑:“你们这群人,越来越像一家人了。”
“本来就是。”他说,“‘清源’不是基金会,是共同体。”
接下来的日子,他白天跟着团队学习基础修复流程,晚上整理“萤火计划”下一阶段方案。他决定将帐篷图书馆升级为“流动美育站”,加入绘画、音乐、手工模块,邀请像李曼这样的年轻艺术家轮驻乡村。他还联系了几位曾受资助的女孩,请她们录制短视频,讲述“谁改变了你的人生”。其中一位叫小舟的盲童女孩说:“我第一次摸到雕塑时哭了,原来形状也可以唱歌。”这句话让他坐在电脑前整整愣了二十分钟。
一周后的深夜,他独自回到第156窟。清霜允许他夜间参观一次,条件是不得触碰任何东西。他站在仕女图前,手电筒的光缓缓扫过她的面容。忽然,他在仕女裙裾褶皱间发现了另一个微小符号??与耳坠上的相似,但方向相反。他立刻拍照发给清霜。十分钟后,她冲进洞窟,呼吸急促:“这……可能是双胞胎姐妹的标记!唐代贵族女子常以对称符号区分身份!”
“所以这幅画,其实是两个人?”
“很可能。”她声音发颤,“我们一直以为是单人像,但从构图看,左侧确实留白过多……如果真是双人像,那就意味着整幅画的理解都要重来!”
两人相视而立,眼中都有泪光闪动。不是因为学术突破,而是因为他们共同触摸到了一段被尘封的真实。
第二天,清霜向研究院提交了重新考证申请。院长看着图像放大后的细节,沉吟良久,最终点头:“启动专项研究。经费问题,你们想办法。”
“我能解决。”井高说。
“这次别拿钱砸。”院长瞪他,“我们要的是严谨,不是速度。”
“我懂。”他认真道,“我可以不出资,但请让我参与过程监督。”
“行。”院长笑了,“你总算学会低头了。”
回宿舍的路上,清霜忽然问:“你说,为什么古人要把名字藏在画里?”
“大概是怕被遗忘吧。”
“可他们又不张扬。”
“所以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证明‘我存在过’。”他望着星空,“就像李曼的妈妈扫街时哼的歌,苏婉教孩子们读的诗,林薇半夜喂奶时的眼泪……没人记录,但它们真实发生过。”
她轻轻靠在他肩上:“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些事,对吗?”
“对。”
临走前一天,他去买了块本地陶片,在背面刻下一句话:“2025年夏,井高至此,见证光复之美。”交给研究院档案室保存。管理员笑着收下:“等你下次来,说不定已经成了文物。”
高铁再次启动时,他打开日记本,写下:
【2025年7月12日晴
今日,我在敦煌学会了“慢”。
慢到能听见颜料剥落的声音,
慢到敢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而不急于擦去,
慢到愿意花三天只为看清一个符号的意义。
清霜说,修复壁画不是还原过去,
而是让过去与现在对话。
我想,我的人生也是如此。
我不是在弥补过错,
而是在重建连接??
与人,与美,与时间本身。
这一程,我不带走任何一幅画,
却带回了整个世界的重量。】
手机震动,是清霜的新消息:【第220窟新发现一处墨书,写着“同行者,勿忘初心”。
我想,这是给你看的。】
他闭上眼,嘴角微扬。

![边疆来了个娇媳妇[年代]](/img/467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