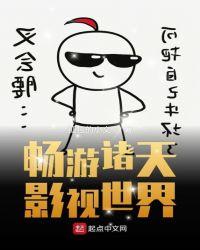笔趣阁>亮剑:我有一间小卖部 > 第一千四百一十三章(第2页)
第一千四百一十三章(第2页)
“这里有台老式留声机……唱片还在……放一下试试。”
片刻后,一段沙哑的歌声响起??《月儿高》,江南民谣,曲调哀婉悠远。而就在第二句唱到“月照花林皆似霰”时,海底突然传来回应:不止一首歌,而是多声部交织,有《茉莉花》《小白菜》,还有那首日语版《奇异恩典》,甚至夹杂着几句听不懂的方言童谣。
“他们在合唱。”艾丽莎喃喃,“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人……他们的声音被海底岩层记录下来,现在因为共鸣,全醒了。”
更令人窒息的是,歌声中渐渐浮现出人名??一个个名字被念出,像是点名,又像招魂:
“张阿妹,1937,南京。”
“金顺姬,1943,济州岛。”
“佐藤美惠子,1945,广岛。”
“陈老五,1942,飞鱼号轮机长。”
每一个名字落下,监听站内便有人无声落泪。那些本该湮灭于战火的名字,此刻穿越时空,在声波网络中重获呼吸。
林突然在通讯中说:“我看见了……墙壁上贴满了纸条,全是求救信、家书、忏悔录……有人用血写的,有人用鱼骨刻的。它们被海水泡了三十年,字迹却越来越清晰。”
“为什么?”徐三问。
“因为……有人一直在读。”
凌晨三点十七分,林返回水面。他几乎虚脱,脸色苍白如纸,手中紧紧抱着那台留声机唱片。
“不是我们唤醒了他们。”他靠在墙边喘息,“是他们一直在等我们听懂。这艘船不是坟墓,是信箱。每一封没能寄出的信,最终都变成了声音,沉入海底,等着某一天,有人愿意蹲下来,把耳朵贴在世界的裂缝上。”
徐三接过唱片,放入播放器。
音乐响起的瞬间,整个小卖部的灯同时闪烁了一下。风铃无风自动,货架上的红糖糕罐子发出轻微震颤,连地下室的“沉默积分”账本也自行翻页,停在最新一页。
只见新增一条记录:
>**林(编号07):因开启沉船记忆之门,积三分。
>备注:沉默非无言,而是积蓄回音。**
与此同时,广播系统突然自动启动,向全岛循环播放这段合唱录音。居民们在睡梦中惊醒,有的披衣出门,有的跪地痛哭,有的则默默打开自家窗户,让歌声流入房间。
哈里斯少校连夜赶来,带来一封加密电报:“九州战俘营昨夜暴动,起因是一名老兵听到《灯》第二集后,当众自述曾参与强征慰安妇。其他囚犯非但未攻击他,反而集体哼唱《月儿高》??据报告,那是许多朝鲜妇女被抓前最后唱的歌。”
“你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他说,语气复杂。
“不。”徐三望着海,“我们只是打开了收件箱。这些声音本就存在,只是以前没人敢听。”
三天后,《灯》第三集《谁在唱歌》正式放映。
影片以海底合唱为背景音,穿插历史影像、幸存者口述、科学家解读,以及那段无法解释的“声波记忆网络”理论。结尾处,镜头缓缓推进至飞鱼号残骸内部,定格在一面布满字迹的舱壁上,其中一行格外清晰:
>“如果你听见这首歌,
>请替我们活下去,
>并告诉后来的人:
>我们也曾爱过,恨过,后悔过,
>我们不是怪物,
>我们只是迷路了。”
放映结束,全场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