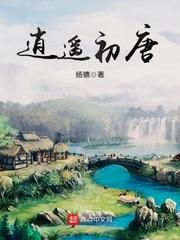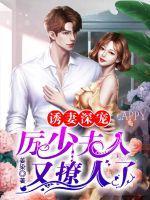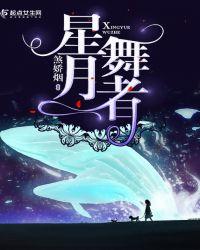笔趣阁>四合院之饮食男女 > 第119章 飞港城(第1页)
第119章 飞港城(第1页)
“豆角好吃,肉不好吃。”
李姝挑剔地用勺子将肉片扒拉开,只挑了碗里的豆角吃。
顾宁只看了她一眼,并没有说什么,倒是二丫很不好意思。
“下次我做嫩一点。”
“没关系,她就是单纯地。。。
雪后的清晨,空气清冽如刀,割开肺腑。王亚娟披衣起身,推开窗时,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却让她精神一振。院子里铺着厚厚的白,像一张未曾落笔的宣纸。岗亭顶上积雪压得微微倾斜,赵建国正拿着扫帚一点点清理屋檐,动作缓慢而专注,仿佛在拂去岁月的尘灰。
她忽然想起昨夜梦中又见了林秀兰??不是站在井边,也不是在花丛里,而是坐在岗亭内,手里捧着一杯热茶,静静望着外面纷飞的大雪。她没说话,只是笑了笑,那笑容温和得让人心头发烫。
王亚娟低头翻开《记事录》,指尖停在冬至那天的记录上。她想了想,添了一行小字:
**“有些声音,不是靠耳朵听见的。它们藏在雪里,落在风中,等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刚合上本子,门铃响了。是苏晴,裹着厚围巾,脸颊冻得通红,怀里抱着一台新打印机。
“调试好了!”她进门就笑,“‘心灵信箱’的自动回信系统终于能用了。以后居民投进来的信,我们会根据内容分类,由志愿者手写回复,再统一打印封装,盖上七星星印。”
王亚娟接过样信一看,纸张朴素但整洁,右下角果然印着七颗相连的小星。“这印章谁设计的?”
“陈伯。”苏晴眼睛亮了,“他说,这七颗星不是装饰,是承诺??七个人守一座院,七个心连一条路。”
两人正说着,窗外传来脚步声。老马拄着拐杖走过,肩上依旧搭着那条油渍斑斑的毛巾,身后跟着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一人拎个小桶,里面装满了彩色蜡笔和胶带。
“童言无忌小组今天值班。”苏晴解释道,“他们负责给‘记忆之匣’更新标签,还说要给每封信配一幅画。”
王亚娟望着孩子们踮脚往玻璃柜贴画的样子,心头一软。其中一个小女孩正认真地描摹一张老照片??那是九十年代社区春节联欢会的合影,林秀兰站在角落,穿着蓝布衫,眼神怯怯的,手里攥着话筒却没开口。孩子在旁边写道:“阿姨你想唱歌吗?我们现在听。”
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这座院子正在长出新的年轮。
下午三点,共创空间召开本月第二次“声音修复计划”进度会。技术人员带来好消息:林秀兰五段语音的合成已基本完成,AI模型经过多次训练,成功还原出一段约四分钟的独白,语气平稳、情感真挚,几乎听不出机械痕迹。
“我们没有添加任何虚构内容。”技术员强调,“所有词汇都来自原始录音片段,仅做语序调整和语法补全。”
投影亮起,全场寂静。
音响缓缓流淌出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我叫林秀兰,住在三排二号。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烧水、做饭、擦地。我喜欢茉莉花,种在窗台,每年夏天都开。孩子们上学时会路过我家门口,有人笑着打招呼,也有人绕着走。我不怪他们……我只是希望,有一天能被人当作‘邻居’,而不是‘那个女人’。
我不是疯子。我只是太累了。
我想过年的时候家里有灯,有人敲门说‘一起吃饺子吧’。
我想我的女儿知道,妈妈不是不要她,是怕自己会伤害她……
如果你们听到这段话,请替我告诉世界:
我存在过,我努力过,我也曾渴望被爱。”**
声音落下,屋里许久无人言语。有人低头抹泪,有人紧紧握住身边人的手。朵朵趴在母亲腿上,小声问:“妈妈,外婆是不是很孤单?”李秀芬搂紧她,哽咽着点头。
“这段录音,”王亚娟站起身,声音微颤,“不能只放给今天在场的人听。它应该出现在每一个角落??公告栏、岗亭外、静语池旁,甚至放进孩子们的课本里。”
众人一致同意。决定从下周起,在每日早间广播播放三十秒精选片段,配以轻柔钢琴曲,名为《听见林秀兰》。
会议结束前,刘红梅带来陈伯的新进展:他已经能通过助听器辨识大部分日常对话,并开始尝试发声练习。医生建议他进行一次公开朗读,哪怕只是几句。
“他自己选了诗。”刘红梅笑着说,“顾城的《小巷》。”
大家都知道那首诗??短短几句,却像一把钥匙,打开幽深的记忆隧道:
**“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当晚,《记事录》新增一页:
**“当沉默者开口,墙就开始变薄了。”**
第二天清晨,黑板更新:
【今日晴转多云,道路结冰请注意防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