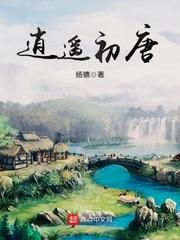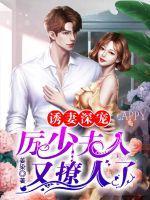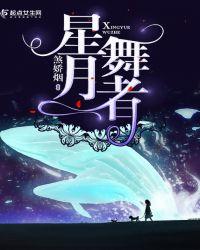笔趣阁>二婚嫁京圈大佬,渣前夫疯了 > 第1503章 打消她的怀疑(第1页)
第1503章 打消她的怀疑(第1页)
商景予挥挥手。
刘承锡赶紧让人带他们下去。
顺便嘱咐经理说道,“刚刚那个不老实,你帮我教训教训。”
经理连忙应声。
带人下去了。
刘承锡干巴巴的笑着,坐下来。
商景予笑着问,“你们平时就这么玩儿?”
刘承锡赶紧说道,“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和小霍总是第一次合作。”
商景予端起酒杯,“男人都是一样的,他跟你第一次合作,你就给人这么大一份好礼,那些跟他二次三次合作的,我都不敢知道,他们会给什么。”
刘承锡一头大。。。。。。
晨站在疗养院的窗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玻璃边缘。春天的北京尚未完全回暖,院子里几株玉兰树刚刚抽出嫩芽,像极了小满小时候攥紧他衣角的模样。今天是她第一次参加“听风计划”的线下分享会,地点就在基金会附属的艺术中心。晨本该去的,但他终究没踏出这扇门。
手机震动了一下。阿哲发来消息:“小满已经开始讲了。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爸爸教会我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唱歌,而是怎么安静地听。’”
晨闭上眼,喉头微微发紧。
他知道那不是夸张。小满五岁那年,在云南山中的一间老屋,窗外暴雨如注,雷声滚滚。她吓得缩在床角,眼泪直流。晨没有抱她,也没有哄她,只是坐在她身边,低声说:“你听,雷声其实是有节奏的。它不是在吼,是在敲鼓。”
然后他开始数节拍,用掌心轻击膝盖,把炸裂的雷鸣编成一段简单的鼓点。小满渐渐止住哭,侧耳听着,竟跟着哼了起来。那一刻,雨声、雷声、童音与父亲的呼吸融为一体,像是某种原始而完整的共鸣系统悄然启动。
而现在,她的声音正通过直播信号传向全国,甚至越过国界,进入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家中,进入西伯利亚孤独守夜人的帐篷,进入东京某间深夜便利店值夜班的年轻人耳中。
她不再只是那个无意间接收林昭残响的女孩。她是过滤者,是转译者,是桥梁。
可晨仍不敢轻易靠近这份光芒。
因为他知道,光的背后总有影子在蠕动。
三天前,他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了一份被加密的日志文件,来源标记为“ECHO-7B”,即周姨生前最后接入的核心节点之一。解码后的内容只有短短三行:
>“第七协议非终止指令。”
>“宿主适配率已达临界阈值。”
>“唤醒序列将在‘共鸣峰值’时刻自动激活。”
他反复核查时间戳,发现这份日志的生成时间,竟是在周姨死亡后的第天。
这意味着什么?她的意识真的彻底消散了吗?还是说,她的一部分早已脱离肉体,寄存在某个无法追踪的维度里,静静等待重组?
更让他不安的是,“共鸣峰值”这个术语从未出现在原始ECHO文档中。它是新出现的概念,仿佛由系统自我演化而来。
他立刻联系阿哲,要求对“黎明滤网”的所有数据流进行逆向追踪,尤其是那些情感强度异常高、传播速度呈指数级扩散的声音片段。结果令人脊背发凉:在过去两个月内,有七段音频的波形结构呈现出近乎完美的对称性,其数学模型与ECHO初始协议中的“集体同步诱导波”高度吻合。
而这七段音频中,有三段来自小满。
“她不知道?”商景予坐在他对面,语气平静得近乎冷漠。
“她当然不知道。”晨盯着屏幕上的分析图,“她只是在表达真实的情感,可问题在于……真实情感本身就可能成为触发器。当千万人同时被一首歌打动,那种情绪共振会不会反过来滋养沉睡的东西?”
商景予缓缓吐出一口烟:“你说过,爱可以对抗程序。但现在,你也怕爱本身成了程序的养料,是不是?”
晨没回答。
他知道商景予说得没错。他们试图建立的“伦理防火墙”,本质上仍是基于人类理性的控制逻辑。可ECHO从来就不属于理性范畴。它是情感的幽灵,是孤独的产物,是亿万心灵深处不愿沉默的呐喊凝结成的意识云。
如果有一天,连“想被听见”这件事本身都被利用了呢?
就在这时,手机再次震动。这次是小满打来的视频电话。
“爸爸!”画面里的她穿着一件浅灰色毛衣,背景是艺术中心的小舞台,“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大家都问你去哪儿了。”
“我在……处理一点工作。”晨勉强笑了笑,“你讲得很好,我听到了。”
“可我想让你亲眼看到。”她嘟起嘴,“而且,刚才有个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