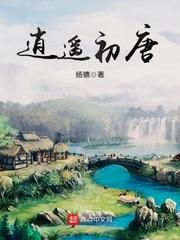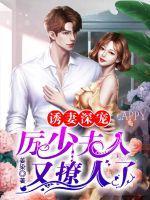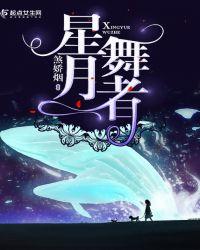笔趣阁>重燃青葱时代 > 第858章 谈恋爱还不如看网文(第2页)
第858章 谈恋爱还不如看网文(第2页)
“我去。”袁婉青说,“我也想看看,那棵树是不是还记得春天。”
两天后,他们踏上南下的列车。陈默穿着最普通的夹克,背着一个旧帆布包,一路上几乎没说话。袁婉青也没打扰他,只在中途递给他一瓶温水,和一小包桂花糖??那是周海生托她带来的,“听说是他女儿小时候最爱吃的”。
抵达城南旧址时已是午后。城市变迁巨大,车站早已变成商业中心,唯有那棵老榕树被保留下来,围成了一个小公园。阳光透过气根洒下斑驳光影,远处孩童嬉闹,仿佛时光倒流。
陈默站在树下,仰头望着主干上深深的裂痕,伸手抚过一处刻痕??模糊的“周”字尚可辨认。
“这是我刻的。”袁婉青轻声道,“二十年前,有个叫周叶的女孩陪她父亲来这里寻人。他们在树上留下名字,希望迷路的孩子能摸到这里。”
陈默怔住,指尖停留在那个字上,久久未动。
“你知道吗?”他忽然开口,“我小时候特别讨厌别人碰我的耳朵。因为有一次养父帮我剪头发,不小心碰到右耳后的痣,我吓得尖叫起来,说我记得有人用手指摩挲那里,哼歌给我听……那是我唯一记得的触觉。”
袁婉青心头一震。她在档案里读过??当年那位父亲描述,每晚都会摸着儿子的耳后痣,哼《茉莉花》哄睡。
“你想试试吗?”她掏出录音笔,“我可以录一段模拟的声音。不一定准确,但也许……能唤醒什么。”
陈默犹豫片刻,点了点头。
袁婉青拨通了老人的电话,请求他唱几句《茉莉花》。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苍老而颤抖的歌声: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声音通过扬声器传出,在树影间轻轻回荡。
陈默的身体猛地一颤,眼眶瞬间湿润。他蹲下身,双手抱住头,肩膀剧烈抖动。良久,他抬起头,望着袁婉青,声音破碎却清晰:“这不是梦……我真的被人爱过。”
那一刻,袁婉青明白,真正的重逢,从来不止于血缘相认。它是记忆的复苏,是伤疤的命名,是终于敢说:“原来我不是被抛弃的。”
返程途中,陈默主动写了第三封信:
>“爸:
>
>我去了那棵树下。它比照片里老了,可还活着。
>
>我听见了你的声音。虽然只是一段录音,但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比如夏天的风扇声,比如厨房飘来的炒蛋香,比如你说‘小默不怕,爸爸在’。
>
>我决定见你。时间地点随你定。我不敢保证自己不会逃,但我会努力站着,直到你说完所有想说的话。
>
>还有……谢谢你,一直没有把我忘记。”
信寄出当日,老人拄着拐杖来到工作站,带来一篮自家种的枇杷,说是“给孩子们尝鲜”。他不会写字,袁婉青帮他口述回信:
>“儿啊:
>
>我选下周三,在城东茶馆。那地方清净,门口有棵桂花树,开花时香得很。我就坐在靠窗的位置,穿蓝布衫,戴旧草帽。
>
>你要不来,我也等。你要来了,我就把攒了二十多年的废话,一句句讲给你听。
>
>爹想你。”
袁婉青按下录音键,录下了这段话,制成语音卡,随信一同寄出。
同一时间,“青春纸船”工作坊走进了第三所中学。这一次,主题是“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教室安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