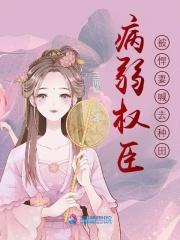笔趣阁>逍遥四公子 > 第1940章 玄武城的天就坐在这里(第2页)
第1940章 玄武城的天就坐在这里(第2页)
“好。”他轻声应下,“我会写。”
守墓人这才露出一丝笑意,转身欲走。林隐忽道:“等等。”
他解开包袱,取出一本手抄册子??正是这些年沿途所见所闻的汇编,尚未命名。他翻到其中一页,递给对方:
>“你也看看这个。”
>
>“去年冬,北境七村遭雪灾,粮绝人饥。一位老妇人打开自家地窖,拿出十年存粮,分予乡邻。有人问她为何不为自己留条活路,她答:‘我男人死在沈将军麾下,临终前说,跟着那样的将军,哪怕赴死也值。如今我能用他的精神救人性命,才算真正活过。’”
>
>“她没读过你的名字,但她记得你。”
守墓人读罢,双手微微发抖,最终单膝跪地,将竹杖插进沙中,深深叩首。
驼铃再响时,夕阳已沉入沙海。
林隐继续前行。他不再急于赶路,也不再刻意寻找什么。他知道,自己早已不是那个独自背负记忆的书写者,而成了万千故事交汇的渡口。
数月后,他来到江南水乡。
烟雨朦胧,小桥流水。乌篷船轻轻摇晃,橹声?乃。他在一座石桥下避雨,见岸边有个少年蹲着写字。纸上墨迹被雨水打湿,晕成一片,少年却不肯收笔,反而咬牙继续写,仿佛要把心事刻进青石板里。
林隐走近,轻声问:“写什么?”
少年抬头,满脸倔强:“我要记住一个人。”
“谁?”
“我师父。他是织工,教我识字、纺线、做人。三个月前,官府强征民丝,他带头抗争,被打断了腿。昨夜,他死了。”
少年声音哽咽,却一字一顿地说:“他说,穷人不是牛马,不该任人抽打。他还说,林先生写的《守望志》里有个木匠,宁可烧掉祖传工具也不替暴政修牢狱。他让我记住:手艺可以丢,骨头不能弯。”
林隐沉默片刻,从怀中取出一方素帕,替少年遮住纸页,挡住细雨。
“你师父说得对。”他说,“我也认识那个木匠。他叫陈九,左耳缺了一角,是因为年轻时救人被刀划伤。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后人,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不想睡着的时候良心疼。’”
少年睁大眼睛:“你……你是林先生?”
林隐没有否认,只是轻轻点头。
少年突然扑通跪下,额头触地:“求您收我为徒!我要把师父的事写下来!我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敢说‘不’!”
林隐扶他起来,语气平静:“我不收徒。但我可以教你一件事??真正的记录,不在纸上,而在你是否敢活得像你写下的那样。”
少年怔住。
“你想写你师父的骨气?”林隐看着他,“那你先站直了,别在他坟前跪着说话。你要走他没走完的路,做他不敢做的事。比如,开一间义塾,教穷孩子读书;比如,把你们织的布印上‘守望’二字,送到每一户人家门口。”
少年眼中泪光闪动,终于重重点头。
雨停了。阳光破云而出,照在湿漉漉的石板上,映出一道彩虹。
林隐离开时,少年追上来,塞给他一个小布包:“这是我娘做的桂花糕……她说,若有朝一日见到您,一定要亲手送上。”
他接过,放进包袱最深处。
这一路上,这样的馈赠越来越多。有时是一碗热汤,有时是一双新鞋,有时只是一句“谢谢您写了那些书”。没有人索要回报,也没有人要求见面。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份感动传递下去。
直到某日,他踏入一座废城。
这里曾是繁华商都,因战乱被屠,十室九空。如今只剩断壁残垣,野草丛生。可就在城中央的广场上,竟有一群孩童围坐,手中拿着碎陶片,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字。
他们写的是:“我想当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