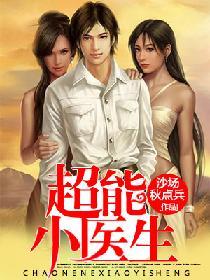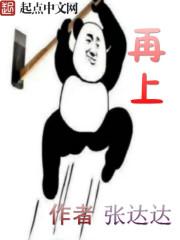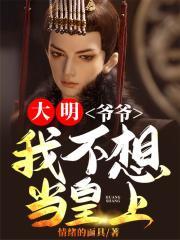笔趣阁>皇叔借点功德,王妃把符画猛了 > 第1666章 会有人死(第1页)
第1666章 会有人死(第1页)
皇上心里涌起一阵接一阵的后怕。
甚至,今晚他都不太敢自己待着,便破例让余妃留在他的寝宫里了。
消息很快传到各宫各殿,后妃众美人各种反应都有。
但皇上此时才懒得理会她们,他这个时候甚至还没有心情去找谁问罪。
包括之前给他提建议说什么月光宝马的杨大人,还有应天监的那些人,什么算好了时辰,算好了地点,什么月光宝马是吉兆的这些事,如今通通都还顾不上去想。
皇上的脑海里一直浮现起那匹马驮着晋王往湖里直接冲下去。。。。。。
阿衡将那张新稿轻轻压在石桌一角,用半块砚台镇住边角。风从山坳里穿过来,吹得纸页微颤,像一只欲飞未飞的蝶。葵儿抬起头,墨笔尖悬在画纸上,一滴浓墨坠下,恰好落在井口中央,洇成一圈深色涟漪。
“阿公,您写的这些话,以后也会被人念吗?”她轻声问。
“会的。”阿衡望着远处田埂上走来的几个身影??那是识字堂刚派回来的两名流动记事员,一人肩挎油布包,一人手提竹篮,篮中盖着一层青荷叶,底下藏着本月各州汇总的情报册子。“只要还有人记得谁曾倒下,谁曾站起,它们就不会真正消失。”
葵儿点点头,低头继续描画碑文的最后一笔。她的字迹尚显稚拙,却一笔一划极认真,仿佛刻进石头的是整个世界的重量。
那两名女子踏入院门时,脚步都有些踉跄。领头的叫柳芽,原是扬州盐户之女,因父亲举报官商勾结被活埋于滩涂,她藏身芦苇荡三日才逃出,后被识字堂收留。如今她已能熟背三十种毒物反应特征,还会用米汤、碱水、蜂蜡调配隐形墨水。她掀开篮中荷叶,取出三本薄册,封面皆以暗纹蝴蝶为记。
“江西那边……又出了事。”柳芽声音沙哑,“不是井水,是粮仓。”
阿衡接过册子,翻开第一页,眉头缓缓锁紧。据报,赣南某县去年秋收入库的三千石稻谷,表面完好,实则长期储于潮湿地窖,霉变生毒。地方官为凑足赋税额度,竟将陈年霉米混入新粮发放赈灾,已有十余名老弱村民食用后呕血身亡。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地医馆被施压,统一诊断为“湿寒入肺”,死者家属若敢质疑,便以“散播谣言”治罪。
第二本册子里夹着一张炭笔图:一群百姓跪在县衙前求验粮食,而堂上官员正把一袋米倒入酒坛,笑着说:“此乃‘清心米’,专治多嘴之人。”
第三本最为沉重??是一份名单。七十八个名字,每一个后面都标注了死亡日期与症状。其中三人,竟是识字堂早前安插在当地做厨娘的毕业生。
“她们临死前留下了记号。”另一名女子低声道,“用指甲在灶台背面划下‘米黑腹痛’四字,还画了个小碗,里面浮着绿丝。”
阿衡闭上眼,指尖抚过那行刻痕般的字迹。他知道,这不只是毒粮案,而是一场针对“拾遗网络”的精准反扑。敌人开始学会追踪信息源头,斩断传播链条。他们不再只惧怕真相被揭露,更害怕普通人学会了如何记录真相。
“我们必须让这件事说话。”他睁开眼,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不是靠哭诉,也不是靠告御状。而是让它自己长出脚,走到每个人的饭桌上。”
当晚,识字堂灯火通明。
阿衡召集所有留守学生,包括尚不能执笔的幼童,每人发一张黄麻纸、一支竹签、一小碟糯米浆。他教她们制作一种特殊的“传音饼”??将写有简讯的纸条卷成细筒,裹上糖衣封入面团,蒸熟后外形与普通糕点无异。一旦遇水或入口融化,内里纸条便会浮现字迹:“你吃的米有毒,请查粮仓编号丙七。”
“这不是骗人吃纸。”他对孩子们解释,“这是把警告变成食物,就像他们把毒药混进粮食一样。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他还设计了一套新的童谣,在原有基础上加入具体线索:
>“大老爷吃白米,小百姓喝泥汁。
>丙七仓里藏鬼气,蒸饭冒绿丝。
>若问谁家娃不吃饭?隔壁王婆咬牙关!”
最后一句暗藏玄机??“王婆”并非真名,而是流动记事员之间的接头代号。凡听到此歌者,若知情,须在三日内向最近的“蓝布鞋女人”通报。
三天后,第一批“传音饼”随商队流入市集。起初无人注意,直到一名孩童贪嘴偷吃母亲带回的点心,嚼到一半吐出纸条,其父对照《拾遗手册》辨认出密语,连夜上报述真司分支。
与此同时,京城再度震动。
太子接到边境快马急报:北方三军营接连出现士兵腹泻、脱发、指尖溃烂等症状,军医束手无策。但一位曾读过《拾遗录》的副将怀疑水源问题,派人检测上游河道,竟发现水中铜离子超标十倍以上。追查之下,源头指向一座新建驿站??正是由工部某侍郎亲信承包修建,而该侍郎之女,恰是皇后生前最厌恶的嫔妃之一。
此事尚未定论,宫中又起波澜。
皇帝召见太子,面色阴沉:“你说,朕这些年究竟是在治国,还是在替一群蛀虫收拾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