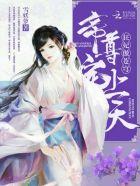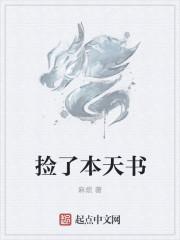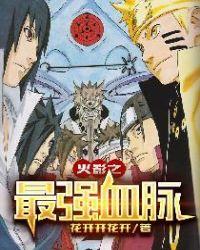笔趣阁>完蛋,我来到自己写的垃圾书里了 > 第904章称心与辩机(第2页)
第904章称心与辩机(第2页)
刘仁一字一句道:“你们烧得尽吗?杀得完吗?”
黑衣首领脸色铁青,咬牙下令:“放火!烧了这客栈,连人带书,统统化为灰烬!”
话音未落,一道身影自屋脊跃下,红裙翻飞如焰,手中长鞭甩出“啪”地一声脆响,精准卷住火把,夺入掌中。
“谁准你们在我地盘撒野?”孙七娘落地轻盈,眸光凌厉,“三年前我能炸塌皇城西墙,今天就能让你们葬身泥沼。”
她身后,数十名镇民手持锄头、扁担、渔叉,缓缓围拢。其中竟有昔日禁军退役老兵、江湖游医、甚至一名盲眼说书人,怀里抱着三弦琴。
“我昨夜刚编了新段子。”盲人抚琴轻唱:“**太庙烽烟起,忠魂唤帝惊。假诏藏宗寺,遗命照丹青。百姓递书檄,将士弃甲兵。九凤铃声断,朝阳出云层。**”
歌声苍凉悠远,竟与雨后初晴的天光融为一体。
黑衣人终于胆寒。他们不过是残党余孽,奉某个妄图复辟的旧臣之命行事,哪里见过这般阵仗?眼看四面合围,首领怒吼一声,转身欲逃,却被赵十三一记飞镖击中小腿,扑倒在地。
刘仁走上前,俯视着他:“告诉你们背后之人??
太后已囚,凤鸣令亡。
若还想掀起血雨腥风,那就尽管来。
但我们不会再躲。”
翌日清晨,镇中广场搭起高台。刘仁将《凤鸣录》全文誊写于大幅白布之上,悬挂于旗杆顶端,供众人围观诵读。镇学先生领读第一章,孩童齐声跟念。那声音清亮稚嫩,穿透晨雾,飘向远方田野。
三日后,又有三批人陆续抵达:一批来自岭南,带来沿海渔民传抄的版本;一批出自蜀中,携有山间隐士注解的经义式评点;最后一队竟是由一名女尼率领,自称“净慧庵”弟子,献上一份以梵文转译的心证笔记,题曰《观妄实录》。
“原来不止我们在做这件事。”孙七娘感慨。
刘仁抚摸着不同材质、不同字迹的抄本,久久无言。这些文字或工整或潦草,或夹杂错字,或添补批注,有的写着“此处当真?”,有的写着“吾父死于此案,今见昭雪,泣血叩谢”,还有一张纸角画着小孩涂鸦的小人举剑砍倒巨妖,旁注:“刘先生打坏人!”
他忽然明白,这本书早已不属于他一人。
它属于每一个为之流泪、为之愤怒、为之奔走的人。
它是火种,也是墓碑;是控诉,也是希望。
半月后,朝廷使者快马加鞭赶到小镇,持节宣诏:
“陛下闻《凤鸣录》民间广传,恐有讹误淆乱视听,特设‘正史校勘局’,邀天下贤达共订定本,藏于国子监,永以为训。”
刘仁接旨,却不接命。
他对使者拱手:“多谢陛下美意。然此书若入宫墙,便不再是百姓之声。请转告天子??
**真正的历史,不应锁在金匮玉函之中,而应活在市井街头、田间灶头。**”
使者默然离去。
当晚,刘仁召集众人,在院中点燃篝火。他将自己手中的原始手稿投入火焰,纸页卷曲焦黑,字迹在火光中跳跃闪烁,如同亡灵最后的低语。
“这是终结,也是开始。”他说,“从今往后,《凤鸣录》不再有‘原本’。它将是千种模样,万般声音。有人会改它,有人会谤它,有人会利用它,但也总会有人守护它。”
他看向赵十三、孙七娘、道士、镇民、学子……
“而我们要做的,不是控制它,而是相信它。”
火光映照下,众人肃立无言。
数日后,一本全新的《凤鸣录》出现在各地书肆。封面朴素,无雕饰,仅有一行小字:
**“据众人口述整理,非官方定本。”**
书中内容与旧版略有出入:删去了部分戏剧化描写,增加了地方志佐证、医案原文、驿卒日记片段,甚至收录了几封普通百姓写给“书中人物”的信??
有少女问孙七娘:“姐姐可曾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