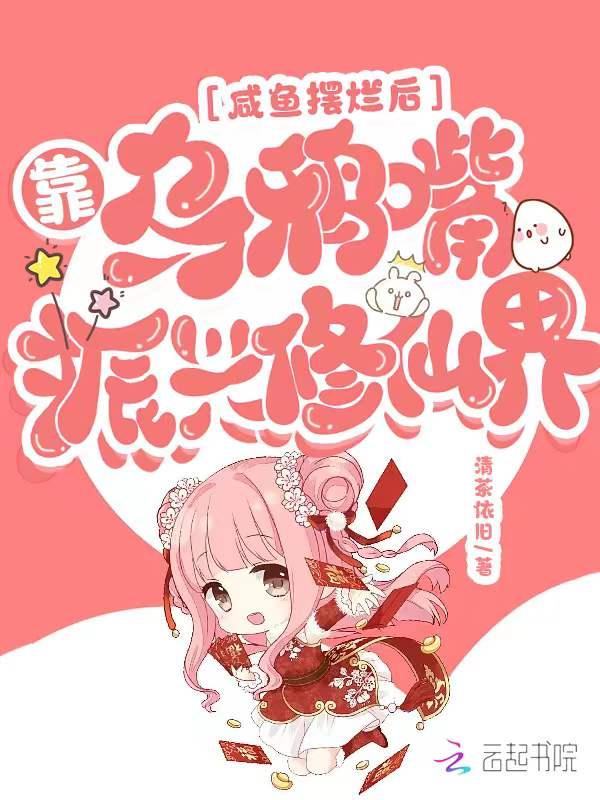笔趣阁>国潮1980 > 第一千六百五十七章 镇店之物(第1页)
第一千六百五十七章 镇店之物(第1页)
上得楼来,完全又是另一番的光景。
千惠美他们还没真正迈步进店,在餐厅领位的引领下刚走到雕花的大门处,就能感到里面的热闹氛围夹杂着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跟着等到真正进入到营业区范围更是了不得。。。
米晓卉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一场罕见的暴雪封锁了华北平原。承志园外的银杏树早已落尽叶子,枝干被积雪压得微微弯曲,像一群沉默的老者低头沉思。屋内炉火未熄,铜壶在炉上咕嘟作响,水汽氤氲中映出墙上那幅泛黄的照片??1982年夏,北大中文系毕业合影,她与顾承志并肩而立,身后是图书馆斑驳的红砖墙。
她坐在书桌前,翻看最新一期《晨读通讯》的校样稿。封面上印着阿依古丽补好的绣帕照片,阳光穿过破洞,洒在“宇宙洪荒”四个字上,宛如新生。编辑加了一句副标题:“文化不是旗帜,而是呼吸。”她轻轻点头,在页脚批注:“这句话留着。”
电话铃突然响起。
是吴小川打来的,声音沙哑:“米老师,我刚从甘肃回来,在张掖中转时听说……青海那边有个村子,全村断电三天,但他们每晚点蜡烛组织孩子诵读《弟子规》。村长说,‘灯可以灭,心不能黑’。”他顿了顿,“我把这段拍下来了,您想看吗?”
“发给我。”米晓卉轻声说,“然后好好睡一觉。你瘦了。”
挂了电话,她起身走到窗边。雪还在下,天地一片素白。她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冬天,也是这样的大雪夜,顾承志高烧不退,躺在医院病床上仍念叨着:“晓卉,你说咱们能不能做点事,让穷地方的孩子也能听见诗?”那时他已确诊肺癌晚期,说话断续如风中残烛。她握着他枯瘦的手,只回了一句:“能。”
如今十年过去,他们点燃的火苗不仅没灭,反而燎原万里。可她知道,火焰越大,阴影越深。
第二天清晨六点,她提前起床,在厨房熬了一锅红豆粥。七点半,李志远、陈知微和林婉清陆续到来,每人带了一包冻梨或一把花生。这是他们多年来的习惯:每逢大事,必聚早餐会。
“教育部新文件下来了。”李志远开门见山,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红头文件,“‘晨读工程’正式纳入‘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求各地教育局设立专项办公室,年度考核挂钩政绩。”
陈知微皱眉:“又要指标化?”
“不止。”李志远苦笑,“昨天我去东城区试点学校调研,发现有老师把晨读时间改成默写测试,还给家长发打卡二维码,一天三次,漏一次就在班级群里通报。”
林婉清冷笑:“这才几个月?理想还没落地,官僚主义先学会了收割成果。”
米晓卉搅动粥碗,热气扑上面颊:“我们得守住底线。不能让孩子们觉得读书是为了应付检查。”
正说着,小张急匆匆推门进来,手里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米老师,出事了!有人冒充‘晨读联盟’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起‘百日背诗挑战’,宣称完成者可获得‘国家认证诵读证书’,收费九十九元!已经有二十多万人报名!”
屋里顿时安静。
“证书哪来的?”陈知微问。
“私刻公章,伪造教育部批文。”小张打开页面,屏幕上赫然挂着一个金灿灿的徽章,“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搞排名榜,按背诵数量排序,前一千名‘天才少年’还能进所谓的‘国学精英营’,线下集训十天,收费八千。”
李志远猛地拍桌:“这是赤裸裸的敛财!打着我们的旗号割韭菜!”
米晓卉却异常冷静:“报警了吗?”
“报了,网信办已经介入。但传播太快,光是相关话题播放量就破五亿了。很多家长信以为真,觉得这是官方项目。”
“那就立刻发布澄清声明。”米晓卉站起身,“同时启动‘真声计划’??我们要让真正的参与者站出来,告诉所有人,晨读是什么,又不是什么。”
当天下午,一段三分钟视频上线。没有特效,没有配乐,只有米晓卉坐在书房,面对镜头缓缓开口:
“我是米晓卉。有人说,你们搞晨读是为了控制思想;有人说,你们卖证书赚钱。今天我想说一句:都不是。我们开始这件事的时候,连个公章都没有,只有一个念头??让人活得有点光亮。如果你的孩子早上读一首诗,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怕;是因为快乐,而不是为了积分换奖品,那我们就没走偏。否则,哪怕挂满金牌,也是失败。”
视频末尾,她举起一本破旧的《唐诗三百首》,扉页上写着一行钢笔字:“赠阿毛,母病逝前手抄,愿儿识字明理。”
“这本书来自贵州一个山村教师。他说,他母亲临终前一夜,一笔一画抄完全书。这样的书,不该变成生意。”
视频发布两小时,转发量突破千万。无数网友自发上传自家晨读画面:东北炕头上祖孙共读《春晓》,江南雨巷里父女撑伞吟诵《枫桥夜泊》,高原帐篷中母亲抱着婴儿轻念《静夜思》。一张张面孔质朴真诚,没有表演,只有生活。
与此同时,公安部门顺藤摸瓜,抓获六个诈骗团伙成员,查封假冒网站十七个。主犯供述,原本只想蹭热度捞一笔快钱,没想到“这帮老头老太太竟真不图利”。
风波渐平,但米晓卉并未松懈。她召集核心团队开会,提出一项新举措:“我们要建立‘晨读伦理守则’,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化、强制化、竞赛化行为。所有合作单位必须签署承诺书,违者立即终止资格。”
李志远担忧:“会不会太严?有些学校靠这些活动拉赞助……”
“那就换方式。”米晓卉坚定道,“我们可以接受捐赠,但绝不允许交易。文化一旦标价,灵魂就打折。”
会议结束当晚,她独自整理档案室。在一摞旧信件中,她发现了顾承志生前写给某出版社的退稿信复印件。那是他最后一次投稿,题为《论诗歌的日常救赎》。编辑回复:“内容深刻,但市场前景不明,暂不予出版。”
她摩挲着那页泛黄的纸,眼眶发热。老顾一辈子都没出过一本书,他的思想,如今却通过千万人的嘴唇活着。
元旦前夕,第一场晴雪过后,承志园迎来特殊客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携代表团来访。他们在校园广场观摩晨读仪式后,提出将“中国晨读模式”纳入全球literacy(扫盲)推广案例库,并建议命名为“LightReadingMovement”(光读运动)。
签字仪式上,外宾问米晓卉:“您认为这一运动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她想了想,指着操场上正在朗读《登高》的学生们:“你看那些孩子,他们读杜甫的时候,不只是在学一首诗,是在经历一种悲悯。当一个人能理解‘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孤独,他就不会轻易伤害别人。这才是教育的本质??培养共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