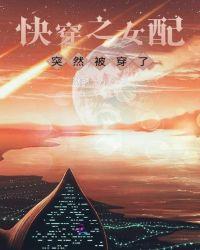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我老婆是天后 > 第1221章股东大会五(第3页)
第1221章股东大会五(第3页)
张友微笑:“她本来就比我强。”
几天后,MER实验室迎来首次公众开放日。首批五十名预约者来自全国各地,有失去孩子的母亲,有退伍老兵,有孤独症儿童家长,也有即将奔赴高原支教的年轻人。
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情绪而来。
一位癌症康复者在共鸣舱中听到了属于自己的旋律??开始是混乱的打击乐,象征病痛折磨;中期转为柔和的吉他扫弦,记录家人陪伴的温暖;结尾则是海浪声与口琴交织,寓意新生。
他走出来时抱着工作人员痛哭:“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苦难也可以被温柔对待。”
另一位盲人音乐学生尝试后惊叹:“我‘看见’了颜色!那段旋律让我感觉到蓝色和金色,就像sunrise照在湖面上!”
这些反馈被迅速整理成报告,送往国家心理健康研究中心。与此同时,国际权威期刊《NeuroArt》发来邀稿函,希望MER团队撰写专题论文。
压力也随之而来。
某财经媒体刊发评论文章《魅影科技是否正在制造“情感乌托邦”?》,质疑该项目过度浪漫化心理学应用,存在伦理风险。“当企业掌握解读人心的技术,谁来防止滥用?”文中如是质问。
资本市场反应两极。魅影股价先涨后跌,投资人担忧战略偏离主营业务。
林志远再次进言:“张总,要不要暂缓对外宣传节奏?至少等商业模式跑通再说。”
张友却在董事会上掷地有声:“MER不是产品,是使命。我们可以慢一点,但不能停。”
会后,他单独约见徐清雅。
“我想推进‘双向共鸣’实验。”他说,“让李冉也试试共鸣舱。”
徐清雅迟疑:“她还小,心智未完全成熟,万一触发深层创伤……”
“所以我不会让她独自进去。”张友望着窗外暮色,“我要陪她一起。”
徐清雅终于点头。
实验安排在周末。李冉得知消息后既兴奋又忐忑:“真的能听到心里的声音吗?”
“不一定听得懂。”张友摸摸她的头,“但至少,我们会更靠近彼此一点点。”
当天下午,父女二人并肩走入共鸣舱。特制双人座椅缓缓升起,神经接口自动适配。系统提示响起:“请选择共享主题。”
李冉想了想,轻声说:“我想知道……妈妈是什么样的人。”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
张友深吸一口气,在输入框中敲下三个字:【晚晴。】
音乐起。
前奏是古筝与风铃的轻响,温婉宁静,一如林晚晴生前最爱的江南春雨。接着,钢琴加入,弹奏一段简单却深情的主题旋律??那是他们婚礼那天,张友为她即兴创作的《晴日序曲》。
随着情绪升温,弦乐组铺陈开来。忽然,一声婴儿啼哭采样切入,紧接着是摇篮曲的哼唱片段。那是李冉出生那夜,病房里录下的真实音频。
乐曲中段,悲剧降临。心跳监测仪的滴滴声逐渐紊乱,音乐随之扭曲、崩塌。但在最低谷处,一段童声清唱悄然浮现??正是李冉五岁时录下的第一段哼唱,稚嫩却充满生命力。
最后,所有旋律融合升腾,化作一场宏大的交响,仿佛无数灵魂携手前行。
舱门开启时,李冉泪流满面。
“原来……妈妈这么爱我。”她扑进张友怀里,“我能感觉到。”
张友紧紧抱住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那一刻,他终于明白,重生的意义不在改变命运,而在修复那些曾因遗憾而断裂的爱。
当晚,徐清雅发来最终分析报告:【双人共鸣成功建立情感谐频网络。父女间的情绪波形不仅同步率达到98。2%,且产生了新的复合旋律??我们命名为《Lian》(链)。建议立项追踪长期效应。】
张友回复:【不必立项。让它自然生长就好。】
他站在阳台上,仰望星空。远处城市灯火如河,近处家中琴房仍亮着灯。李冉还在练琴,一遍遍重复那段新写的曲子。
他知道,那将是属于一代人的“心灵回声”。
而他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