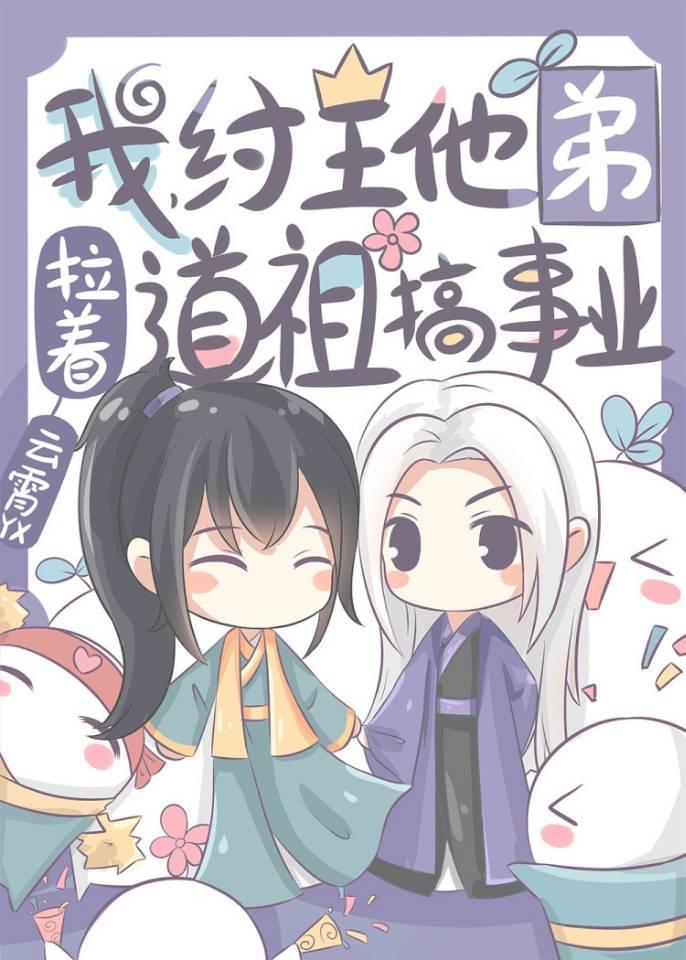笔趣阁>千禧:我真不想当大导演 > 第828章 无敌无非无攸(第4页)
第828章 无敌无非无攸(第4页)
几天后,LINStudios迎来一位特殊访客。
老人拄着拐杖,衣着朴素,眼神却明亮。他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文轩,八十二岁,晚年致力于乡村阅读推广。他带来一本亲手编纂的册子??《孩子的声音诗集》。
“我把一百段‘回声计划’里的原话改编成了短诗。”他翻开一页,轻声念道:
>“他们说我疯了,
>可我只是想让妈妈看看我的奖状。
>她打工六年,
>回来第一件事是骂我成绩差。
>我把奖状折成纸飞机,
>从楼顶扔下去??
>风听见了,
>现在,你也听见了。”
林有攸眼眶发热。
老人笑着说:“语言是最温柔的革命。你们做的,不只是心理干预,是在重建这个时代的耳朵。”
临走前,他留下一句话:“记住啊,不要总想着拯救谁。有时候,让人‘被听见’本身就是救赎。”
这句话被林有攸刻在了新落成的“倾听广场”石碑上。
冬天到来时,“回声计划”正式接入国家心理服务平台,成为全民心理健康体系的一部分。每一个拨打12355青少年热线的人,都有机会接入“匿名倾听志愿者”网络,获得一对一语音陪伴。
而王小军,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草稿,暂定名《拾声者》。镜头跟随他走过桥洞、工地、救助站、山村小学,记录下那些曾被认为“不该发声”的人如何一点点找回自己的声音。
拍摄间隙,他常独自坐在录音室,反复听那段十年前自己录下的即兴对白??那时他还是一名电影系学生,对着麦克风喃喃:“我想拍一部所有人都能看懂的片子,哪怕只有一个观众流泪,也算值得。”
如今他终于明白,有些片子不必上映,有些观众无需看见。只要声音还在传递,光就在流动。
春节前夕,林有攸收到一份快递。
打开是台老式磁带随身听,附信写着:“这是我儿子留下的。他重度抑郁三年,几乎不开口。直到听了‘回声计划’里一个男孩讲‘我也害怕黑’,他第一次主动要了耳机。现在他会说‘我想试试’。谢谢你们,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孩子。”
磁带上贴着手写标签:《第一次说话》。
林有攸放进机器,按下播放。
几秒杂音后,一个稚嫩的声音轻轻响起:
“爸爸……新年快乐。
我想……活下去。”
他抱着随身听站在阳台上,雪花静静落在肩头。
远处,城市灯火通明,万家团圆。
他知道,还有无数盏灯下的角落藏着未曾出口的痛。但也正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蹲下来,说一句:“你说,我听。”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声音。
缺的,是那一句“我在”,真的抵达了对方心里。

![边疆来了个娇媳妇[年代]](/img/467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