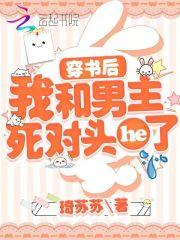笔趣阁>大秦镇天司 > 第870章 赵洲不愧剑洲之名(第2页)
第870章 赵洲不愧剑洲之名(第2页)
紧接着,十二支陶笛共鸣而起,音波交织成网,笼罩整座山巅。孩子们开始齐声哼唱《庶民谣》,声音稚嫩却坚定;阿禾敲响青铜铃铛,清越之声划破长空;百名弟子依次吹奏各自所学之曲,旋律杂而不乱,层层叠叠,汇成一股浩荡声流。
苏篱闭目,继续吹奏。她吹的是《静音公主祭歌》的变调,节奏更快,情绪更烈,像是在召唤什么,又像在驱逐什么。
忽然,祭坛上的“噤魂铃”微微颤动。
一声脆响,第一道红绳崩断。
风骤起,卷起满山紫藤花瓣,如雨纷飞。
第二声,第二道符?自燃。
第三声,铃舌竟自行复生,轻轻晃动,发出极细微的一声“叮”。
苏篱猛然睁眼,陶笛高举,全力吹出最后一个长音??那是“宫”音的极致,纯净、明亮、穿透一切。
“轰!”
一声闷响,铜铃炸裂,碎片四溅。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内,一名正在抄写《民声录》的官员突然捂住喉咙,剧烈咳嗽,继而发出沙哑的“啊??”声。他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手。
同一时刻,岭南织女言坊中,一位失语半年的老妪突然站起,指着天空喊道:“我说话了!我能说了!”
北疆戍楼之上,老兵含泪吹响号角,声音洪亮如钟。
全国二十四州,数百名“哑疫”患者在同一时辰恢复言语。太医署记录显示,无人服药,无人施针,唯有一共同征兆:发病当日,皆曾听闻风中传来隐约笛声,似远似近,如诉如诉。
消息传回苍梧岭,苏篱已疲惫至极,倚靠在紫藤架下沉睡。阿禾为她披上外衣,静静守在一旁。
三日后,太子遣使亲至,带来御笔亲书的诏书:
“自即日起,废除一切与言论限制相关之旧律,追查‘哑疫’幕后主使,无论官职高低,一律严办。另设‘言脉监’,专司监察全国言语自由状况,遇异常沉默,立即上报。”
使者还带来一件礼物??一块玉佩,上面雕着一支陶笛,背面刻着四个小字:**声归于民**。
苏篱没有收下玉佩,只让使者带回一句话:“请殿下记住,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谁能说话,而在于谁不再害怕说话。”
又过了半月,沈知白再度上山。这一次,他不再是孤身一人。身后跟着十余人,有太史局老吏、地方县令、江湖游医,甚至还有两名曾隶属镇天司的退役执剑使。
他们带来一份名单??三百二十七人,全是疑似参与“哑疫”阴谋的旧势力成员。其中不乏三品大员,更有皇亲国戚。
“我们查到了一条暗线,”沈知白沉声道,“当年镇天司虽被裁撤,但其核心人物并未伏法,反而转入地下,组建‘缄默会’,代代相传,誓要‘净化天下之音’。他们利用古籍中的禁声之术,结合药物与心理操控,制造‘集体失语幻觉’,让人误以为是疾病。”
苏篱听完,冷笑一声:“果然,他们从未相信过人民能好好说话,所以宁可用邪法让他们闭嘴。”
“我们要怎么办?”一名年轻县令问道,“若公开揭露,恐引发动荡;若姑息养奸,民心必寒。”
苏篱望向观言台,那里正有几个孩子在练习吹笛。她缓缓道:“你们还记得,我为什么坚持教第一个词是‘我饿了’吗?”
众人点头。
“因为它小,但它真实。现在,我们也该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她转身走进屋内,取出一本新册子,封面写着:《缄默录》。
“把这些人,一个一个记下来。不要急于定罪,而是去查他们做过什么,听过什么,压制过哪些声音。等证据确凿,就让每一个受害者站出来,当着全城百姓的面,说出他们的名字。”
“你要让他们被听见?”沈知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