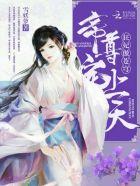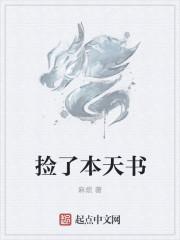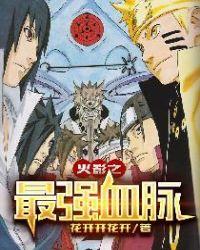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大隋刚登基,你说这是西游记 > 第499章 玄鸟金纹(第2页)
第499章 玄鸟金纹(第2页)
他知道,流沙河到了。
玄奘解下行囊,在河边盘膝而坐。他并未急于渡河,而是取出炭笔与粗纸,开始一笔一划写下沿途所见所闻:岭南孩童的梦、青铜箱中的信、皇宫血池的记忆洪流……他写得极慢,仿佛每一道笔画都在对抗某种无形之力。
三日后,他写下第一段祭文:
>“第一位亡者,姓李,名守仁,蜀中人氏。二十岁考中秀才,立志教化乡里。三十五岁被征入‘清忆司’,负责销毁民间族谱。四十二岁,因私自保留一本记载饥荒真相的村志,被判‘忆罪’,沉河。临刑前高呼:‘历史可以被烧,但良心烧不尽!’”
话音刚落,河面剧烈震动。一具枯骨缓缓浮出水面,双手仍戴着镣铐,头颅微仰,空洞的眼窝似乎在凝视天空。
玄奘继续念:
>“第二位,王氏,无名,仅知其夫战死边关,她独自抚养三子。因每逢清明必哭诉亡夫事迹,被视为‘传播仇恨’,列入清除名单。四十七岁那年,被人灌下无忧丹,从此痴傻,终日抱着空摇篮哼歌。死后亦不得安葬,抛尸于此。”
又一具骸骨升起。
接着是第三位、第四位……每念一人,便有一具尸骨浮出,排列成桥状,横跨河面。玄奘的声音早已嘶哑,指尖因长时间书写裂开流血,但他未曾停歇。
当第一百零八位亡者的名字被念出时,整条流沙河突然干涸,河床裸露,尽是白骨与破碎木牌。一座由骸骨构成的拱桥静静矗立,通向对岸。
玄奘拄杖起身,缓步踏上桥面。每一步落下,脚下白骨便化为尘灰,随风消散。待他走到尽头,回望身后,桥已不见,唯余一片平坦沙地,仿佛从未有过亡魂阻路。
他不知的是,就在他渡河之时,终南山巅,哑女手中的青笛突然断裂。碎片落地瞬间,竟长出一株嫩绿新芽,转瞬开花,花形如灯,散发柔和光芒。
守心会众人惊愕抬头,只见忆井上方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月光直射而下,照在双芯灯上。灯光骤然暴涨,投射出巨大影子??那影子里,赫然是玄奘的身影,正走在一条通往西方的漫长道路上,身后跟着无数虚幻人影,皆含笑相随。
“他开始了。”一位老弟子低声说。
“不。”哑女第一次开口,声音沙哑如风吹枯叶,“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开始了。”
同一时刻,西牛贺洲深处,某座笼罩在紫雾中的高塔之内。
一名身披黑袍的老者端坐于水晶棺前,手中握着一面监控万象的铜镜。镜中正映出玄奘渡河的画面。他脸色阴沉,猛地将镜摔在地上,厉声道:
“又是‘记得’的力量……当年天机子败于此,今日也要重演么?”
身旁走出一名白衣女子,面容绝美却毫无表情,眼中似有万千星辰流转。“主人不必忧心,”她轻声道,“我已经派出了‘忘音使者’。只要他奏响‘寂灭曲’,哪怕是最坚定的记忆,也会化作虚无。”
老者冷笑:“去吧。让东土来的和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忘记’。”
数日后,玄奘进入一片戈壁荒漠。此处寸草不生,空气干燥得令人窒息。正午时分,远处传来悠扬琴声,清越动人,闻之心神宁静,竟让人忍不住想放下一切烦恼,就此长眠。
玄奘心头警兆顿起,立刻堵住双耳,默诵《心经》。然而琴声无形,竟能穿透皮肉,直入识海。刹那间,他脑海中浮现出种种幻象:母亲的笑容消失了,师父的教诲模糊了,甚至连“阿福”这个名字也开始变得陌生……
“不好!”他猛然醒悟,“这是要夺我记忆!”
危急关头,他咬破舌尖,以剧痛保持清醒,随即打开《忆行记》,疯狂翻页。书中文字竟自行燃烧,化作点点金光环绕周身。光芒所及之处,幻象退散。
与此同时,书中跳出新字:
>“忘音使者,原为东汉乐官,因创作《安魂调》导致全国百姓集体失忆,被天雷劈中,魂魄囚于琴内千年。今受忘经阁操控,专杀怀揣记忆前行之人。
>破法唯有二:一曰‘共鸣’,以真实情感回应其曲;二曰‘断弦’,亲手毁其命器。”
玄奘喘息未定,已见前方沙丘后走出一人??白衣胜雪,怀抱古琴,面容俊美近乎妖异。他轻轻拨动一根琴弦,天地为之寂静。
“旅人,”他微笑,“你为何执意背负痛苦前行?放下吧,安宁才是归宿。”
“安宁若建立在遗忘之上,不过是另一种死亡。”玄奘盯着他,“你说‘安魂’,实则是灭魂。我不会让你再害一人。”
说罢,他竟盘膝坐下,从怀中取出一支竹笛??正是当年念生遗留之物。
他不懂音律,却将心中所有记忆倾注其中:小全子拄拐巡塔的身影,阿福父亲写信时颤抖的手,哑女吹笛时清澈的眼神,还有那场覆盖整个时代的雪……
笛声起初杂乱,渐渐凝聚,竟与对方琴声形成对抗之势。两股音浪在空中交锋,沙石飞扬,天地色变。
忽然,玄奘想起一事??《守心志》中记载,阿福生前最爱听一首童谣:
>“月亮出来亮堂堂,
>照见我家老屋墙。
>娘亲做饭烟袅袅,
>爹爹归来脚步忙。